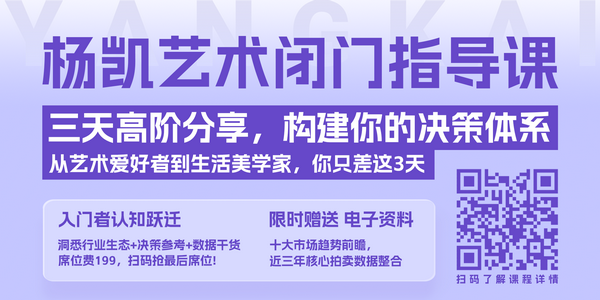内容提要 :在新时期的美术界,媒介何以成为问题?回答该问题,本文认为以1986年兴起的“波普热”为切入点,能够得到一定的解释。1985年的劳生柏个展是一针催化剂,直接触发了美术实践和理论界从关注艺术的主题性意义,转而开始讨论新的艺术媒介。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艺术媒介所蕴含的技术元素被降低了,作为低技术媒介的现成品之功能被抬高了。早在这个时期,现成品组合的偶然性被赋予传统的“禅”“道”内涵,从而具备了文化合法性。“波普热”的意义主要体现为80年代中后期逐渐展开的媒介拓展实验,这让国内美术界在没有经历一个典型的媒介时代之前,就跨越到了后媒介时代,或混合媒介时代。
关键词 :波普热 劳生柏 媒介
受到劳生柏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影响,新时期的美术界掀起一股被称为“波普热”的创作潮流,无论之于艺术实践还是艺术理论,这个潮流中的关键问题便是关于媒介的讨论。任何艺术形式都天然地依赖特定媒介,这个道理似乎不证自明。但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对某一艺术媒介的自觉意识,则具有历史性。媒介问题首先与技术相关。摄影技术的出现,曾引发一场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媒介之争,最终以两者的交叉融合而告终,之后电影、电视、录像和计算机等媒介不断独立为新的艺术门类,同时,运行在这条路线图上的艺术也往往被冠以“新媒体艺术”之名。技术之外,媒介还与代表审美现代性的艺术自律相关。这一点显然在格林伯格编织的现代绘画叙事中最为突出。他认为各艺术门类最终要回到自己那独一无二的媒介特征中去,于是提出了绘画之本质在于画布“平面性”的论断。当然,在技术因素和艺术自律性之外,一个时代对于艺术媒介的自觉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比如社会需求,左翼木刻和新年画运动的兴起,正是木板和印刷这一媒介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典型体现。相比之下,本文选择聚焦一个偶然的展览事件,即1985年11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考察在该展览影响下的“波普热”中,美术界如何开启了新一轮有关艺术媒介的讨论,个别艺术家的实践又从哪些方面进行了回应。
一、从主题性意义到媒介
无论我们将媒介的定义建立在新技术之上,还是建立在存粹的物理对象之上,直到1985年底的“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之际,艺术媒介本身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被美术界特别提示出来。也就是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内,艺术媒介的特殊性并不是新时期中国美术界首要讨论的问题。伤痕和乡土美术主要争议在内容,只有在罗中立的《父亲》中才涉及到表现技巧的问题,这个也是通常所说的由“画什么”到“怎么画”的转变。而关于后者,也只是在1985年的“观念更新”讨论中才最终凸显出来。除此之外,由吴冠中的《内容决定形式?》一文引发的抽象美大讨论,也只是停留在形式美的层面,未进入到绘画作为媒介的特殊性的讨论。实际上,伤痕和乡土美术,还有形式美,都只停留在画面内容层面,而没有进入后来我们所谓的画框、基底和颜料的物质性层面。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可能在于前两者的内容是主题性的,而后者的内容是纯形式的,或更接近装饰性。
在“波普热”到来之前,艺术的媒介问题一直受到遮蔽,作品的主题性意义依然是创作和评价一件作品的主要焦点。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事件值得关注:一个是“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另一个是1985年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在一般新时期的现代艺术史叙事中,因为遵循着“哲理性”“观念性”与“理性”的逻辑,张群、孟禄丁的《在新时代》和耿建翌的《灯光下的两个人》(图1)作为这两次事件中的代表性作品,被归纳入中国现代绘画发展的主潮之中。这种归类有一定道理,因为两幅作品也是当时两个展览中争议最大的作品,与整个时代的美术观念转型相关。《在新时代》与《灯光下的两个人》虽然表现的主题大相径庭,但是所有关于这两件作品的话语却集中在内容和意义方面。作为当时展览的评委,袁运甫先生如此解释《在新时代》:“尽管画面出现的是圣经故事里的人物——亚当和夏娃这一对创世纪的男女,但它象征和寓意的恰恰是又一个新的世纪的诞生。这是一个打破已有传统、冲破框框和险阻,奔向美好未来的新时代”[1]该作品使用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各类标志性的符号,最终被赋予正面意义。相比之下,《灯光下的两个人》则没有受到如此礼遇,因为作品意义不明确,描绘的内容也被判无效:“在画面上看不到今天时代的人物。也许作者想得很多,但画面给予我们得只是冷冰冰的面孔,僵化了的人物。”[2]有关这两件作品的评价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件绘画描绘了什么,这些内容又有何明确的、积极的意义是那一时期美术界的关注焦点。但在后来,恰恰是这些没有具体意义的“哲理性”绘画成为现代艺术史书写的主要内容之一。

图1,耿建翌,《灯光下的两个人》,布面油画,1985年
如何评价那种“冷冰冰的面孔,僵化了人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当时被展现出来,一种方式是赋予这类无意义的冷漠以正面评价,认为艺术家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冷静思考;另一种方式则是回到绘画的媒介特性中来。作为耿建翌的指导老师,金一德的观点属于后者,他认为:“有教员提出这张画看不懂,从而引起了争论。它说明由于油画创作长期来习惯于带有文学性的构思处理方法,当别人想改变一下这种方式,而强调绘画本身的语言时,许多人反而不习惯了。”[3]试图将绘画区别于文学,这是西方现代绘画媒介自觉的首要一步,无论耿建翌是不是在强调油画作为媒介的特殊性,显然我们在艺术史书写的过程中把这一视角给过滤掉了。之所以能够引起争议,都是因为《灯光下的两个人》这件作品本身具有的折衷性特点,耿建翌既没有特别强调绘画本身的语言特点——由此避免滑入先前形式美的装饰化困境,又没有强调绘画中的故事性,而是将图像悬置在了抽象和文学性之间的某一点。
相比起《灯光下的两个人》在媒介特性问题上的模棱两可,艺术家张骏的《1976年4月5日》则直接引入照片这种新媒介。该作品曾获“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但在后来的艺术史书写中,几乎被忽略掉了。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件作品的主题性意义太过明确,在那个时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按照张骏自己的说法,这件作品主要采用了“复印、泼彩、实物粘贴等方法”,是他“想用现代技法来表现中国青年题材的一种尝试”。[4]从作品整个构成来看,主要是照片为主,加以不同媒介的混合使用,首先是一张四五青年的照片被不断复制,然后拼贴至整个平面;其次是在拼贴的表面泼彩;最后是粘贴一面实物镜子,让观众可以在看作品时也看到自己的镜像。《1976年4月5日》可算是新时期绘画中最早凸显媒介问题的实验,布满画面的照片复制品恰好强调了照片作为媒介本身的复数特质,右下脚那面镜子,又提示出照相机作为复制机器的镜像功能。
作为展览的评委,马克、袁运甫和徐冰都注意到了《1976年4月5日》这件作品对新媒介的敏感性。马克认为该作品在与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因为使用了照片复制和拼贴,显得“另辟蹊径”,“独出心意”。袁运甫具有预见性地提出不久后美术界掀起的“波普热”:“(作品)互为融合的设想,尽管取自西方波普艺术手法,但丝毫没有别扭或因袭之嫌。”[5]同为版画出身的徐冰,更是看到了这件作品在媒介方面为艺术创作打开的广阔前景:“本没有形式和画种的区分,不管运用什么手段,只要它保留了那种与科学公式不同的艺术感染力,它就是有效的表现形式。”[6]很可惜的是,尽管评委们都看到了作品中的新媒介因素,但最后都将主题性的意义作为最终验证这件作品成功的要点。也就说,作品的媒介最终被意义淹没,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过多的讨论。这如同立体主义的实物拼贴,因为一直遵循造型的整体原则,而未显示媒介的独立特性,只有到了达达主义,现成品和照片作为新媒介才艺术的核心。
二、偶然性与“禅”“道”——被接受的低技术媒介
在劳生柏将自己的那些混合媒介的作品置于中国美术馆之前,新时期的美术界从来没有将媒介作为讨论的焦点,那些涉及媒介的作品,也被主题性的意义遮蔽掉了。到此为止,我们有必要再次思考,我们在新时期美术发展中谈论媒介时,到底是在谈什么?美国批评家罗莎琳·克劳斯将马塞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的作品看作“后媒介时代”系谱的主要源头时,其实预设了一个“媒介时代”。如果“后媒介时代”可以与当时的“后现代”相对应,那么“媒介时代”则与“现代”相对应。现代主义的媒介问题,被克劳斯总结为格林伯格本质主义的“平面性”,而后现代主义的“媒介”则属于递归结构(recursive structure),它否定本质主义的独特性,在自我差异化(self-differing)的过程中形成开放、多义的集合体。[7]所谓递归结构,通过克劳斯的解释,其实就是指艺术内部各类元素之间建立的规则,其反之又创造了结构本身。例如,克劳斯认为,绘画的媒介特质不是平面性,而是色彩按照一定规则在平面上的组合。所以,绘画作为媒介的特性,不应仅仅是那块物质性的平面,而是平面之上各元素的组合方式——这个结论显然是结构主义式的。显然,国内新时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实践并没有经历绘画上的“媒介时代”,而是经由《1976年4月4日》这件作品,在劳生柏个展的刺激下,直接跃入了“后媒介时期”,或者“混合媒介时期”。因此,我们在讨论“波普热”前后的媒介时,不是在讨论油画、国画、版画和雕塑分别对应的媒介特征是什么,而是在讨论艺术的新型结构,而新的图像生产技术和新的物质材料对完成这类新结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图2 ROCI 封面
劳生柏的个展于1985年11月18日至12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英文直译名为“劳生柏海外文化交流”(Rauschenberg Overseas Culture Interchange),简称“ROCI”,(图2)中文展名被定为“劳生柏作品国际巡回展”。展览期间发行了一本画册,封面图像是一只背负地球仪的海龟,很明确地阐释了“海外文化交流”的主题。在中文标题和英文标题的微小差异之间,我们会发现展览意图与接受之间的错位。关于劳生柏举办这次展览的意图,在一篇名为《意向书》的短文中表述得很明确,即是通过各种媒介,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媒介包括录像、照片、录音、素描、版画以及画册等。劳生柏在每个国家展出的作品不尽相同,因为他会用在不同国家创作的新作品置换旧作品。[8]于是劳生柏的展览充当了一座信息枢纽的角色,将不同地域的信息置于展览空间中进行交换。这一文化交流的意图在很多作品中被展现出来。画册中刊印了47件作品,除了少数抽象画和实物装置外,照片和丝网版画为主要媒介,它们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例如大部分由照片转印后的拼贴作品包含了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信息,艺术家在不同国家的经历也转换为作品,《鲁迪的房子——ROCI委内瑞拉》《天气预报——ROCI墨西哥》《女像柱的行列I——ROCI智利》(图3)等作品就携带了众多国家的文化信息。

图3 劳生伯,《女像柱的行列I——ROCI智利》,1985
为了向观众解释劳生柏的作品,展览策划者做了充分的文本工作,展览画册刊登了一篇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的长文,详细介绍了劳生柏的各类艺术样式,包括集成艺术(现成品组合),丝网印刷和石版画等。但是,新时期的美术界对劳生柏作品携带的信息并不感兴趣,艺术家和理论家真正感兴趣的是他自由使用混合媒介的创作方法,准确地说,是作为物质的媒介结构关系,而非作为技术的媒介。劳生柏的很多图片拼贴实际采用了溶剂转印和丝网印刷技术,但在实际接受过程中,技术的因素被降低了,现成品和照片拼贴的物质性媒介特征被放大了。这样的接受情况,很快在媒体上反映出来。展览刚刚结束的当月,新一期《中国美术报》刊登了部分艺术家和理论家对劳生柏展览的看法。其中老一辈艺术家郁风总结道:“我对劳生柏的创作意图的理解就是‘化腐朽为神奇’。”“腐朽”当然是指劳生柏作品中的日常现成品,或废物拼贴,而“神奇”则是指艺术。对郁风来说,作为媒介的现成品带来的最大冲击应该是指出了艺术门类的局限,“否定一切绘画和雕塑的框框。”[9]在《中国美术报》举办的作品座谈会,也反映出国内美术界对现成品的兴趣,理论家水天中指出了新媒介带来的新突破,当然他当时用的词汇是“新材料”和“新技巧”:“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往往是和新的材料,新的技巧同时出现的,相形之下,我们许多画家用古典的技巧、传统的工具、材料从事现代绘画的实验,这必然限制了形式突破。”[10]其余的与会者,如刘骁纯、孟禄丁、吕品田、梁江等都谈到了现成品带来的观念冲击。在这个上下文中,我们今天讨论的“媒介”,在那时实际等同于物质材料——日常生活的现成品/图像。这些日常物品在劳生柏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为创作艺术的主要媒介,在此基础上,造型艺术各门类之间的界限受到了挑战,更进一步,便是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受到了挑战。
20世纪60年代,阿瑟·丹托看到了安迪·沃霍的《布里洛盒子》,不断追问艺术何以成为艺术的问题。同样的情况,因为劳生柏展览的刺激,也在中国新时期的艺术界发生了。对艺术与生活边界的质疑,说到底,是因为“新”媒介的出现。这里的新,不是技术之新,而是低技术的旧物品进入艺术界产生的“惊奇感”。当然,我们并没有产生类似丹托和乔治·迪基那样的“艺术惯例论”,因为劳生柏的国际名声,自然赋予了那些低技术的旧物品以艺术的身份。新时期艺术理论家将“低技术的旧物品如何成为艺术”的问题,转换成为了“低技术的旧物品如何创造了审美经验”的问题。在《什么的艺术和应该的艺术》一文中,作者王鲁湘和李军从杜威的《艺术作为经验》的论点出发,论证了劳生柏的作品之所以是艺术的理由。在他们看来,低技术的旧物品成为艺术,是因为根据“审美经验是艺术作品的本质”的观点,这类媒介的组合结构能够产生出“一个完满的经验”,即审美经验,所以,可以被理解为艺术。[11]美学作为新时期文化界的一门显学显示出它的解释性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媒介的问题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审美高度,而没有继续深入讨论媒介本身。
相较于将低技术的旧物品审美化的倾向,部分理论家和艺术家强调了这类媒介之间非理性、无意识的结构规则,这一点更值得关注。吕品田和李家屯(栗宪庭的笔名)在这方面讲得比较清楚。前者强调劳生柏“一幅作品的众多素材之间并没有什么情节上的逻辑,似乎多是偶然的、下意识的择取,许多作品的标题与作品本身也没有什么具体联系。”[12]媒介选取的偶然性因素直接导致作品意义的消解,这让李家屯认为艺术家在和中国观众开了一个大“玩笑”:“在劳生柏把生活中的东西随便拿来,并游戏般地做些处理的作品面前,任何对精神意念的传达,都显得过分严肃,而且中国观众又是那样地执着、严肃的态度对待劳生柏的作品,这便是我所说的劳生柏作品展所产生的‘玩笑’效果。”[13]中国观众的“严肃性”与劳生柏的“玩笑”恰好对应了新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主题性意义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论,《1976年4月5日》中有目的性的照片和实物组合,以明确的意义遮盖了媒介本身的问题。而在时隔不久的劳生柏作品中,媒介携带的偶然性的结构原则终于浮出水面。
偶然性和无意义还不是新时期美术界对混合媒介的全部认识,1986年9月26日远在厦门的黄永砯在《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一文中,进一步回应了劳生柏展览提出的问题。[14]虽然厦门达达的艺术实践受劳生柏作品的影响,这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在理论方面,他们却把这类混合媒介——抛弃媒介特殊性——的方法与“道”和“禅”联系起来,进而又关涉到了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潮流。先是把“道”的无所不在与作为媒介的日常物品联系起来,文章阐述道:“劳生柏的一件艺术品可以以任何长短时间存在,可以用任何材料,在任何地方,为任何目的,以及任何归宿的看法,更符合于‘道’的无所不在。”其次是“禅”与日常物的关系:“就像禅宗既把一尊雕像的释迦当作佛,又把其当作一块烧火的木料,当作佛是为了联系生活的世界,当作木是作为超越生活世界,在这一点上佛和艺术是作为生活世界中一个无法改变的意义而存在的。”[15]最终在黄永砯的理论中,劳生柏作品中的媒介结构特征被用中国文化的语词完全展示出来,那些一定要赋予劳生柏作品审美特质的理论,在“道”和“禅”的偶然性、无意义、非审美和非形式的对比下,似乎显得过时,又不得要领。
为什么新时期的美术界对劳生柏的作品如此感兴趣?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对“新”的追求。在发表的一张照片中,当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版画教师徐冰,正在仔细观察劳生柏的一件现成品装置,现成品作为媒介显然对他而言,充满了新奇感。在若干年后,回忆起劳生柏的冲击,徐冰坦言:“我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劳生柏的作品,因为没有任何参照物可以对比。”[16]如果劳生柏的作品代表新,那么同一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那次朝鲜作品展,对于徐冰来说,就是旧的代表。当徐冰想要创作“新的艺术,但新的艺术是什么东西,其实又不知道”时,现成品的出现显然为他提供了某些灵感。[17]意义退去之时,媒介则凸显出来。徐冰不久后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析世鉴》,便通过抹除意义,将印刷和文字的媒介展示出来。按照理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的提示,我们在艺术作品中追求新,实际是在追求某种新的意义,新的文化价值。当我们不再期待从艺术作品中抽离出某种不变的真理时,“创新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某些人们经常见到和相当熟悉的东西的价值发生了变化。”[18]在这个基础上,劳生柏作品的现成品和混合媒介,让新时期的艺术家发现了创新的可能。而创新可能性的基础,在格罗伊斯看来,恰恰在于艺术作品能否成功地适应传统。显然,在黄永砯为厦门达达正名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这方面尝试。他将1983年赵无极画展中的“道”“禅”思想与劳生柏画展相比较,得出结论,“前者属于前现代主义,后者则属于后现代。”[19]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赵无极之类的作品试图解释“道”“禅”文化时,劳生柏的作品已经成为“道”“禅”本身。这样一来,劳生柏作品展给予新时期美术界的新奇感,被顺利地转换为中国词汇,与80年代的中西之争,艺术的民族化问题融为一个整体。
三、不彻底的波普热与媒介拓展的遗产
劳生柏展览结束后,受其影响的艺术家立刻行动起来,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一系列模仿劳生柏作品的艺术实践。高名潞在1986年4月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中最早将这类现象归结为“波普热”,在谈到这一现象时,他写道:“各地很快出现了一批 ‘小劳生柏’,对于这个称号,他们并不难为情……其实,早在劳生柏展览之前的一二年内,各地已相继出现这种材料拼合和集合物的作品。走到这一步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而劳生柏展览只不过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催化剂而已。”[20]或许由于评论与实践的相隔时间太近,高名潞也只是概括地描述了一现象,没有进一步做过多的价值判断。就作品本身来说,艺术家们在实践中感兴趣的元素,与理论家的观点一致,他们都留意到了劳生柏作品中作为低技术媒介的现成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技术要求低,模仿起来也方便,于是,现成品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媒介一时间在各地蔓延开来。

图4 池社,《作品2号-绿色空间的行走者》,1986年 图片来源:高名潞等著,《‘85美术运动》-1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波普艺术,其媒介特征有两个彼此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大众化的图像或物,二是制作这类大众化或物所需要的复制技术。劳生柏带给中国观众的,除了上述波普艺术的两方面外,还有达达艺术选取现成品的偶然性原则。但是,在短暂的“波普热”中,艺术往往过于强调现成品带来的“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放弃了对某一具体媒介的深入研究,从而导致大批昙花一现的实验性展览和作品。例如山西太原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展览中各类现成品材料纷纷登场,展览参与者直言劳生柏展览曾给他们启示,追求艺术的平民性和朴素性,作品“即兴而作即兴拆除”。[21]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类艺术实践恰恰如作者所希望,过去之后,鲜有痕迹留下。浙江“池社”的青年艺术家们,在《作品1号:杨氏太极系列》(图4)中,用报纸和晒图纸剪出巨大的太极拳套路图,张贴于公园的青砖墙上。这件作品完成后,朱青生以《把艺术还给人民》为题,强调该作品的意义在于与观众的平等对话。虽然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也符合波普艺术的一贯原则,但却掩盖了“池社”艺术家进行媒介拓展的实验价值。他们将报纸剪贴拓展至真实的社会空间,在这一点上,“池社”艺术家的实践已经远离了劳生柏的现成品和图像拼贴。 当然,在1986年的上下文中,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波普热”的问题所在。署名苏晓华的作者在《不彻底的波普热》一文中,指出那些模仿劳生柏,使用现成品,并“宣称要将艺术归还人民”的艺术实践不合时宜,这个观点显然直指朱青生对“池社”作品的评价。[22]但是,作者推崇的艺术是什么?他认为谭力勤的《万物化生》(图5)是一件佳作,该作品使用了现成物品,如毛笔、砚台、印章和墨块等,是针对传统中国画的揶揄和讽刺,相比其他拘谨、小气和松散的作品,它充满战斗性。但从今天的视角看,《万物化生》虽然看似转换了传统中国画的媒介呈现方式,但因其依赖于低技术的现成品,依然没有出奇之处。正如文章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这类现成品的组合,远不如谷文达在当时以水墨为媒介进行的文字实验有视觉张力。

图5,谭力勤,《万物化生》
所以,新时期劳生柏作品给予我们的遗产,不是那些随意组合的现成品本身,而是由现成品带来的媒介拓展实践,这类实践或突破了原本以画种为核心的媒介本体论局限——虽然很难说我们是否真正经历过一个媒介本体论的讨论,或者采取完全不同的新媒介,但无论如何,重视技术或技巧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对于前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谷文达和徐冰,二人也都因为关注汉字的变形组合被频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二人都从汉字入手,分别对国画和版画依赖的传统媒介进行拓展。谷文达先是采用巨大的尺幅,将水墨的浸晕效果推向极端,然后引入错字,赋予中国画以观念艺术的特征,最后把水墨语言置入立体空间,让其装置化了。用当时谷文达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中国画的材料媒介还是很有特点的,把它和西方现代观念融合在一起并推到一个极端,这就是我近两年准备要干的。”[23]在后来谷文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谓中国画的媒介特点主要体现在墨与宣纸方面,西方的现代观念则是拼贴的方法与空间的配置。在文字方面,谷文达与徐冰做了同样的工作,他们先后消解文字的意义,从而让文字作为媒介本身独立起来。同样,二人也没有完全放弃各自领域的技巧,例如《析世鉴》依然可见作者的木刻技术,书籍也是经典的宋代装帧方法。对于谷文达而言,避免使用现成品这类低技术媒介,是他有意避开杜尚和劳生柏的策略。 在劳生柏展览中,除了现成品和照片,艺术家其实还带来了电视和录像,只是不过因为技术条件限制,“波普热”中一直没有艺术家尝试这类媒介。直到1988年,“池社”的艺术家张培力拍摄了作品《30x30》(图6),新时期的美术界才看到依托新型技术媒介的作品。我们现在很难说录像艺术的产生是“波普热”的直接结果,但是,新型媒介的出现确实符合1986年以来“池社”的媒介拓展逻辑。《30x30》并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记录了艺术家不断用502胶水粘合破碎玻璃的过程,时长180分钟。恰恰是因为没有故事,这件录像作品才体现出早期录像艺术的媒介实验效果,无意义的过程充分彰显出影像媒介的时间性特征。
小结
媒介因其携带的技术属性,以及与艺术自身语言的关系,自然与艺术的现代性发展联系在一起。新时期国内艺术界正在逐渐分离绘画的语言和意义的关系,在这样一个艺术不断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媒介的问题才逐渐萌生出来。自20世纪初开始,艺术界就不乏关于中西艺术媒介的争论,这些论题在新时期的艺术界也依然引起关注。但正如本文所论,对于单一物质媒介的讨论,新时期美术界并没有进入一个西方所谓的“媒介时代”,而是在“波普热”这一现象中,直接进入到了“后媒介”时代。以作品《1976年4月5日》为例,我们明确看到媒介如何被意义遮蔽。在劳生柏的个展中,我们看到了意义的退场与混合媒介的出场。随后掀起的“波普热”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夹杂在一起,为后来国内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尚若我们可以说,艺术观念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的更新,那么“波普热”中形成的媒介意识——从低技术媒介的偶然性到基于技术的媒介拓展实验——则可以总结为我们今天当代艺术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原文发表于《美术》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