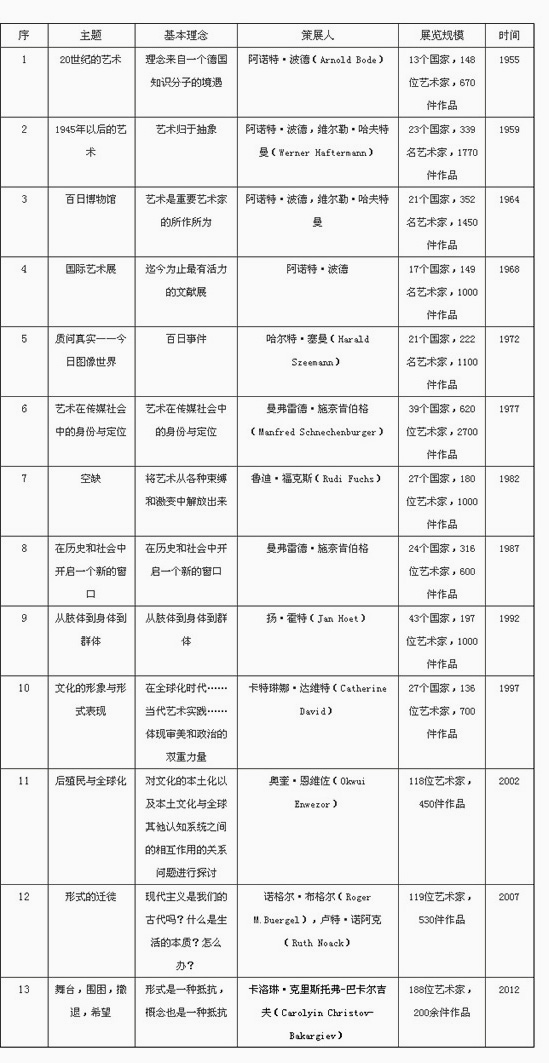
很明显,如果说1955年第一届dOCUMENTA意在朝向历史的话,那么从1959年的第二届开始,它便逐渐转向未来和可能的趋势探问。dOCUMENTA的创始人也是当届策展人阿诺特•波德公开表明,“第二届文献展面对的不仅仅是显示从1945年其发展的过程,去有力强调那些最为重要的大师,更应该关注那些跑在经典艺术之前的新概念的发展。”这一理念持续至今。我想,这也是一直以来它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所在。对很多人来说,都期冀从中看到一种可能的方向。

当然,事实也不尽然。虽说其中大部分的主题和理念都有明确的导向感,但也有个别恰恰是去导向感的,或者说,在它这里导向或趋势及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反而成了一种束缚和障碍。譬如1982年的第七届,策展人鲁迪•福克斯提出“将艺术从各种束缚和激变中解放出来”,展览没有确定某个具体的主题,只是表明这样一种去导向或趋势化的理念和态度。福克斯在致艺术家的邀请函中这样说,“我们经历了许多展览:优雅的、乏味的、政治意味的、神秘的……这个展览又将阐明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失望,感到我们的作品不知何故被某种力量操纵着:事情总会牵扯到某些文化背景、历史记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把这次展览看做一个‘故事’,甚至想过以此作为展览的主题:‘第七届文献展——一个故事’。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主题。”因此,往届都将关注点放在一些艺术运动,或是放在艺术家身上,而福克斯却把重心放在作品上。如果说dOCUMENTA意味着一种可能的方向的话,那么对福克斯而言,这个方向就是没有方向。
不过,之后的8至12届,都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主题。而且,不同策展人,他(她)所提出的理念和主题与其知识背景、关注方向,甚至身份认同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第11届的策展人奥奎•恩维佐提出的主题是“后殖民与全球化”,这实际上与他的非洲裔身份不无关系,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叙述中国历史一样,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印度裔这一自我身份认同的色彩。某种意义上,卡洛琳也是。虽然展览中没有明确的线索和意指,但她对于贫穷艺术的推崇,对于边缘实验的发现,包括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问题的深度关注等等,都与她的知识背景、学术视野、视觉趣味乃至身份认同不同程度地有着一定的潜在关系。
卡洛琳明确了四个关键词:舞台、围困、撤退、希望,事实是我们很难从中探得其明确的导向何在。在这点上,它似乎更接近无主题、无方向感的第七届。且两届的重心都不是艺术家和策展人,而是作品。就像卡洛琳略显含混的解释一样,她说:“什么处于围困之下?什么处于希望当中?什么是撤退或退场?当我在舞台上表演时我在干什么?我所感兴趣的是,上述四种处境其实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始终是互相重叠,彼此区别但又同时发生的。”不同于福克斯试图将艺术从政治、社会等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卡洛琳显然是有态度的,她依然坚持艺术就是政治,认为形式和概念都是一种抵抗。而且,我们虽然无法整体上确知她针对的问题或抵抗的对象是什么,但从局部或就某个具体的作品而言,都不难找到其中暗含的所指。因此,作为展览,dOCUMENTA(13)是开放的,但每一具体作品却并非走向空无,大多都有一个隐性的态度和反思。
“物”的解放与形式的打开
看得出来,迄今关于dOCUMENTA(13)的评论更多还是围绕艺术媒介的拓展,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评述。其中提及最多的是“物”和“声音”。比如对于“物”的重申,有人说“物质开始是个重要命题的时刻”。而对于声音的强调则更多来自新媒介和高科技的介入带来的丰富新奇的感官体验。比起往届,本届展览的确突显了“物”和“声音”。问题是,当我们将讨论视域放在文献展历史的维度上时,我们发现,也不尽然。相对第七届而言,或许反思的对象略有差异,但就反思本身而言,二者之间并无差异。本届展览中“物”的凸显与其说是基于媒介、材料与形式的实验需要,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观看机制对于认识论和知识性体制的反思和瓦解。说到声音,实际上早在1992年,扬•霍特策划的第9届便以装置、光影、声音、形象、行为等艺术形式为主。可见,声音在本届凸显并不稀奇。稀奇的倒是各种媒介的结合与混搭。在我看来,其之所以得以凸显恰恰不是因为单纯的声音本身,毋宁说是它与其他媒介包括空间、展场的生动互应。比如位于老火车站展场的William Kentridge作品The Refusal of Time便是由多屏影像、声音、机械装置综合配置的一组大装置,各种媒介之间互相调动,极大可能地调动和拓展了观众的体验感和观看思维。

因此,对于dOCUMENTA(13),我们可以就其中的具体问题或某个具体作品作出分析和判断,但任何整体化的判断特别是具有预言性的过高评价都难免有失偏颇。事实证明,一旦将其置于dOCUMENTA的历史维度,会发现,我们所强调的比如物、声音、技术、政治等等,在dOCUMENTA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因而还不足以成为支撑它成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最主要展览之一的因素。这也说明了,无论是不是有意所为,但dOCUMENTA的确有它相对稳定的一面。而且,你会发现,卡洛琳实际上在展览中还是极尽可能地在回应dOCUMENTA的历史。主题馆一楼展厅中的莫兰迪曾经参加1955年的第一届文献展,还有1959年第二届的参展作品朱利奥•冈萨雷斯(Julio González)的雕塑,包括第五届文献展上最终未能展出的阿里吉埃罗•博埃迪(Alighiero Boetti)的Mappa也出现在主题馆,等等。而卡洛琳对于形式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上届主题“形式的迁徙”的回应和延续。上届展览的序言中这么写道:“由于这是一个关于现代艺术的展览,尽管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我们坚信这是必须的,因为许多形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也可能会在未来延续下去。”之所以选择重申现代主义,目的就是为了找回已经被商品吞噬了的艺术形式及其美的秩序。再看卡洛琳身上,其实也不乏明显的形式色彩和概念意识。只不过在她这里,形式并不是自足的,它还是一种政治,一种抵抗。上届策展人诺格尔•布格尔虽然没有明确他的抵抗意识和政治自觉,但和卡洛琳一样,对于当代艺术的商业化、娱乐化和奇观化,都坚持一种强烈的抵制。
因此,很多评论者将视角置于“物”(在这里,实际上声音也是“物”的一部分)本身,而在我看来,卡洛琳凸显的不仅仅是“物”,或者说,单纯靠“物”本身个体还不足以实现从知识体系的解放,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前缀——形式和概念,它们更像是一种解放的方式。这里的“物”绝非是现成品意义上的“物”那么简单甚至有些粗糙,而是每一件作品及其展场空间的布置,都经过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精心设计过。因此,形式、概念的介入一方面将“物”景观化了,进而重新赋予“物”新的语境,另一方面,“物”的形式化与概念化实际上也是对于形式与概念本身的一次打开。与其说这是“物”的解放,不如说是形式的解放,概念的解放,或者,是一种观看的解放。它打开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并重建了一个新的“外在”的世界。正是因为形式、概念与“物”的共同解放,才使得个体的有效介入和体验成为可能。
诚如卡洛琳所说的,“一个世界性的、与物质、物品、其他生物和它们视角的内部互动,会使知识成为非象征性和非拥有性的,取消了所谓所有权的概念形式,与此同时,它提供一种使时间慢下来的形式的可能性,一种物态的时间。”在此,不论“物”,还是形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供一种让时间慢下来的可能。这种“物”可能是一幅画,可能是一部影像,也可能是一张照片,一件雕塑,一个装置,一件瓷器,一场表演,或是一段声音……作为一种形式或概念存在,它是一种延迟或是时间的凝滞。在这里,展览、作品、艺术家、策展人、观看者之间,不再是谁支配谁、谁指向谁,而是一种内外充满活力的共构、互动和融合过程。于是,“当你近看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一种深思的过程,或者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活动,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边思维边想象的方式,一种直到让这种粘滞性的体验将你的心智与眼前的物质融合的过程,慢慢地,可能地,从一种所谓的客体的,外在的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不是最终从一种有洞察力但却也往往分离于客体的主体到达……”,正是在这种共构与互动的体验中,我们方可探得一种缝隙,一种例外,一种偶然,甚或一种暂时的消失,临时的停滞。而这已然构成了对于围困我们的二元知识体系的反思与抽解。
不同的是,卡洛琳选择的不是简单、粗暴的方式,或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一种缓慢的、逐渐的温和且不乏均衡的方式。因此,时间还在,只是被缓缓压缩或慢慢褶曲。概念、形式的物化或者说物的概念化、形式化,使得观看者的体验和介入也变得缓慢起来,直至将自己让渡给物、形式或概念,而不再受自我意志和知识的支配或干涉。窃以为,体验性和介入性无疑是本届文献展对于观看本身的一次拓展。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在表演和声音类作品中。老火车站Michael Portnoy的作品特意在取消了灯光且一片漆黑的旧仓库堆了一个土堆,半球形的舞台设在土堆顶部挖的一个坑内,惟一的光线来自顶部的土坑。观者若要观看和参与,必须通过梯子爬上土堆才能到达舞台,和三位表演者进行互动。位于Hugenottenhaus后面的临时建筑内是Tino Sehgal的作品。这是一件暗室,观众进入后除了能隐约看到晃动的几个观众身影和偶尔的轻言低语外,就是一片漆黑了。渐渐地,你会听到一些歌声,看到一些跳舞的身影,甚至会令观众产生些许莫名的惊惧和惶恐。Ceal Foyer的作品在FRIDERICIANUM一楼一间特设的空间内,里面墙上只是挂着一副白色的小音响,音响内反复播放着Tammy Wynette的一句副歌:“我要继续下去,直到我做对了。”歌声环绕在空荡荡的白色展厅,加上隔壁吹来的丝丝凉风,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验。除此,还有Karlsaue公园中的Janet Cardiff & George Bures Miller、Ryan Gander、Gabriel Lester的作品都给观众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虽说这些作品的重心是声音,但展场与空间赋予声音新的语域使其深具形式感。特别是展场空间本身就具有与作品所指相应的历史语域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语域的重叠和压缩,时间体验恰恰是在压缩的缓慢展开中实现的。譬如Bunker im Weinberg中Allora & Calzadilla的作品,OBERSTE GASSE中喀布尔艺术家的作品,还有Theaster Gates对Hugenottenhaus的改造,等等,莫不如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主题馆二楼的Kader Attia的作品The Repair,他将战争中受伤士兵的肖像以原始木雕的方式塑造出来,且一并展示出来。同时,将有关的历史文本用螺丝钉钉死在铁架上,旁边影像播放着战争中受伤士兵肖像的原始图片。此时,原始的,历史(战争)的,当下的,多重的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看似被压缩为一种永恒的纪念,但历史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展开和呈现。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卡洛琳的四个关键词,将这一形式解释为,它既是一个共享的舞台,显现了一种当代状况,也是一次集体的撤退,同时,还揭示了一种围困,一种孕育着希望的围困。
卡洛琳说:“一些作品会谈论艺术的毁灭,另一些则展示毁灭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有贝鲁特国家博物馆被毁掉的雕塑残片;柬埔寨年轻艺术家Vandy Rattana的照片——照片展示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一枚炸弹留下的弹坑,如今已经变成一道奇特的风景;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画的瓶瓶罐罐以及真的瓶瓶罐罐——他给这些实物也涂上了一层油画颜料。因此,这里存在一种语域的转移,从艺术品的虚构领域转向其外部世界。就某种意义而言,上述这些都是一个概念。但它作为概念就像象形文字也变成概念一样。你没法用它——你不能把它数码化;不能把它做成PDF发给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抵抗,概念上的抵抗,抵抗的对象是认识论上的封闭和知识生产。”这样一种解释和说明意味着,在卡洛琳这里,“物”的解放并非依赖于单一的形式自足,毋宁说是在一种互应和关系中展开的,这样一种关系构成了一种立体的形式和不可平面、不可复制的概念。还比如,意大利艺术家Giuseppe Penone的作品,在FRIDERICIANUM一楼的半圆厅中摆放了他两块“石头”,同时,在他此前(2010年)已经植于Karlsaue公园中那棵树上,卡了一块与之相类的巨石。实际上,这一举动同样暗示了一种语域的转换,从博物馆到公共空间,单纯地看,可能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形式,然而,当建立这样一种语域关系的时候,它挑战的不再是形式或概念,而是我们的观看方式,或者说,我们对物的体认和理解方式。所以,有时候dOCUMENTA可能只是一种提示而已,至于作品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观者自己去阅读相关文献,然后才可有所体会。而当我们对形式和概念有所体认的时候,形式就不再是形式,概念也不再是概念,它们已经被彻底打开了。
就像卡洛琳提出的“舞台”、“撤退”、“围困”、“希望”这四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一样,展览似乎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若欲从中理出一条或几条清晰的线索,基本没有可能。但是,不少作品背后,事实上还是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叙事,甚至,一些作品之间,也不乏某种叙事性关联的暗喻。因此,当作品被展出时,不仅意味着原初叙事被彻底开启,且具有生成新的各种叙事的可能。对于dOCUMENTA(13),我们其实很难铺陈一段大叙事,不过可以探得无数小叙事。这其中,有些可能是艺术家、策展人意欲建立一种内在的关联而用心设计的,有些也可能是观看者体认所得的,但都具有一种失却方向的生长性。殊不知,这也恰恰导致了一种去中心的均质化结果。而去中心或均质化常常隐含着弥散的陷阱。或者说,形式和概念的打开固然重建了物我关系,但也不乏消解展览质感的危险。这更像是一个悖论。我想,dOCUMENTA(13)的本意或许就是要以“弥散”的形式和概念诉诸抵抗。这与几乎同时举行的第七届柏林双年展激进的行动主义恰好形成了两个极端,尽管都意在抵抗。
景观、均衡与抵抗
迄今为止,无论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学者的争论,抑或普通观众的意见,皆已表明,对于dOCUMENTA(13)而言,诸如展览本身是好是坏、政治观点正确与否此类的判断其实已经失效。也许,针对某件作品,或某个展厅(或单元)的主题,我们会做出一个具有明确价值倾向的判断,也可以做出艺术语言之好坏的评价,可是,当你面对下一个作品,或者,进入另一个展厅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的判断在此已经被冲淡或消解。就像主展厅FRIDERICIANUM一楼的部署一样,一方面两边大厅的作品将空间彻底让渡出来,另一方面,半圆形的中厅内竟然拥塞了近30件作品。一方面,展览空前地将“物”从历史原境的(认识)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现实及政治自觉又赋予“物”以新的语域。一方面粗砺、激进的历史与政治感不断化解着极具匠心的景观及其审美意味,另一方面,作品形式与展场部署的精致与考究又无形中在削弱这一历史与政治感。一方面物化的形式与景观构成了一种消极的政治,另一方面植根于现实与历史的诸多话语本身又显得很是积极。……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均衡感,揭示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内在的张力及其复杂性。均衡看似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景观,但恰是这一形式或景观,消解了封闭的单向度政治,而将其置于一个开放的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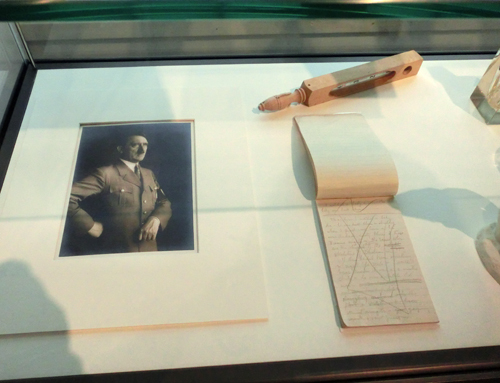
均衡并不意味着策展人卡洛琳没有立场。基于“作为政治的艺术”这一前提,她明确提出了dOCUMENTA(13)的四个基本主题:舞台,围困,撤退,希望。因此,如果说她有立场,那么也已内化在这四个主题之内,而很难将其归为左,或右。坦白说,如果没有这四个主题的提示,我们还无法找到其内在的所指及其关联。反之,通过作品的梳理以为可以找到四个主题之间内在的关联,但最后发现,即便有关联,也不是线性的或谱系性的,而更多是一种不确定的同构或共时性的展开。在此,舞台即围困,撤退即希望。舞台的建立本身是为了将从围困中解放出来,撤退本身也是为了诉诸某种期待和希望。
卡洛琳几乎调动了卡塞尔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镇能够调动的所有空间资源,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多自由的舞台。而艺术的介入,与其说是开启了这些空间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不如说是重新置入当下现实感及其政治针对性。在这里,艺术的表演不是依赖舞台,更不是被舞台所束缚,而是激活舞台,使其成为自由表达异见的空间,或就是作为异见本身。展场及其历史语境本身因此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卡洛琳对于绘画的态度也体现在这里。说到底,不是卡洛琳有意拒斥绘画,而是绘画本身在卡洛琳这里已经很难自足。似乎只有与其他媒介包括展场空间生成有效关联的时候,才能将绘画从固有的观看方式和视觉逻辑中解放出来。看得出来,卡洛琳对绘画的兴趣要么是朴素的甚至略带原始感的自然绘制,要么是倾向极简又极为精巧的形式构成或概念表征。比如Jeanno Gaussi、Gerard Byrne的作品,绘画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无疑是绘画及其部署对于空间的调动。
前文提及的位于Bunker im Weinberg的二战遗留下来的防空洞既是Allora & Calzadilla作品的展场,也是作品的核心部分。作品并不难理解,洞内深处安放的影像中的秃鹫和刺耳的声音,及其政治所指与二战极端的右翼倾向形成了话语的互应,它不仅意在激活历史,而且深具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如今天还在不时上演的战争、屠杀与暴力等无疑是他自觉反思及抵抗的对象。或许,它还潜在地回应了OBERSTE GASSE中喀布尔艺术家的专馆。甚至与主题馆中的Goshka Macuga、Kader Attia的作品,包括位于老火车站的Clemens von Wedemeyer的影像也具有某种关联。事实上,不仅只这些,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类似可能的关联,而且,这一主题本身似乎就可以构成一条线索,或一张dOCUMENTA(13)的话语版图。
在访谈中,卡洛琳数次提到来自芝加哥的艺术家Theaster Gates。过去的将近一年时间里,Theaster Gates生活在由逃亡到卡塞尔的胡格诺派教徒所建造的Hugenottenhaus,他用各种废弃的材料重新装饰了这座老建筑。卡洛琳告诉我们,这件作品是主题“撤退”的一部分。正是在向历史或个人身体记忆的“撤退”中,蕴藉着反省和抵抗,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希望。我想,卡洛琳之所以将其植入具有不同历史语境的空间内,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打开空间所具有的历史语境,及其与当下及未来发生碰撞、对话的可能。
有人批评强势的卡洛琳支配甚至主宰了此次参展艺术家的创作。对此,卡洛琳自己并不回避也不否认,坦言近200件作品中160件是根据她的要求和建议创作的。若没有她的建议,很多作品估计会有不小的出入。事实上,对于卡洛琳而言,艺术家甚至包括策展人已经退居其次,或者说,艺术家只是作品的一部分,而策展人也只是整个展览的组成部分之一,真正的重心还是作品和展览,及其所调动或针对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恰恰是作品和展览本身,赋予或带出了艺术家、策展人的文化政治身份。也因如此,在参展艺术家中,大多还是无名的艺术实践者,Kristina Buch还只是一名在校学生,年龄最小的喀布尔艺术家Mohsen Taasha只有21岁。不消说,是不是艺术家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的实践是否具有足够的问题感和针对性。所以说,不少人纠结于是不是中国艺术家或者说有多少位中国艺术家参展,这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这个身份是否是展览所针对的问题。显然不是。

如前所言,在卡洛琳这里, dOCUMENTA(13)是一种形式上的抵抗,概念上的抵抗,抵抗的对象是认识论上的封闭和知识生产。我想,这也是她为什么如此强调艺术对于“物”本身的解放的因由所在。事实上,艺术的物化本身就是为了将艺术还给艺术,惟其如此,才可能从主体的认识逻辑或框架中解放出来,进而以一种更为开放的视野回应历史与现实。开放意味着卡洛琳所谓的政治不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其实在展览现场,我们也很难看到曾经主宰艺术界、知识界近半个多世纪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话语实践,而是将其从中抽离出来,不再被任何知识、体制、逻辑所束缚,所围困,在一种充溢碰撞与紧张的均衡形式与概念中,回到政治的原点:异见。套用卡洛琳的话说,在这里,抵抗本身就是政治。
特别声明:本文经作者独家授权于99艺术网,未经99艺术网书面许可,请勿转载。有意与99艺术网内容转载等业务合作者,请与媒介部联系(电话:010-51374001转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