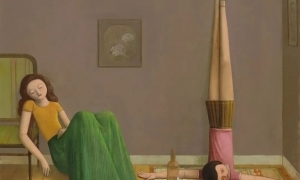地方美术文化的写作意义
――《成都美术志》编修笔记
张颖川
《成都美术志》的编修工作具有挑战性
位于西南部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历来就有辉煌的修志传统,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人东晋史学家常璩编著的《华阳国志》被中外中学界称作为“中国地方志的初祖”。就美术而论,成都人从来不缺记录本土历史的热情,北宋黄休复撰写的《益州名画录》成为了一部最早记载地方区域画家创作状况的地方绘画史。以后西蜀地方绘画史稿的编辑整理就连续不断,宋代范成大著《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著《蜀名画记》,明代曹学佺著《蜀中广记·画苑记》,民国6年(1917年)成都存古书局出版四川国学院教授罗元黼编辑的《蜀画史稿》,民国34年(1945年)成都崇礼堂印制薛志泽编著的《益州书画录》,1956年,江梵众、陈蓉峰撰写了《清代蜀中画家传略》。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成都文化艺术志编修工作,负责整理编辑成都美术史志资料,这项工作对于我是一件“公务”,同时又是责任,历史的责任,延续一千多年来成都编写地方美术史的责任。而在“公务”和“责任”中还具有挑战性。它挑战所谓“地方”“地域”文化的认知意义,也挑战历代前辈们关于记录地方区域画史、绘事的写作方式。1996年,由我主笔撰写完成了现代《成都文化艺术志·美术篇》。2006年一部记录1848年至1999年成都美术历史的《成都美术志》出版发行。
我在《成都美术志》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如果说撰写一本全国范围内的史书,坐在图书馆里,或坐在一个电脑旁边就可以收集到大部分材料,那么要撰写一本有关地方史志,就必须走出资料室,到一个又一个的团体中间,一个又一个人群里,一个又一个学院内,甚至一个又一个家庭中去。”《成都美术志》根据四川省会城市的特点,从地理范围上超越现在行政管辖区域的成都市区,拟定为成都地区 “大成都”概念,要收集驻成都地区省属系统美术单位发生在成都地区的艺术活动,许多文献资料源于四川省文化艺术志美术篇和成都市文化艺术志美术篇,但要编辑出版一本独立的美术志还需要大量的采访收集,特别是对个人的访问,这占据了美术志编修工作量的三分之二。美术创作是个人行为,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城市,所谓的“书画家”“书画展览”非常多,并多发生在民间社会各地,民国时期到60年代的资料因历经各政治革命运动的清洗散失较多,甚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原作品都不容易找到。当时这还不是工作的难度,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从一大批民间“个别”环境中收集来的零乱史料里分析整理出秩序。当然首先严格按照地方志编修工作程序要求作“长篇”记录,但记录的标准是什么?尤其是第一章“创作”,哪些材料可以录用,哪些材料不能录用,哪些人的活动可以记载,哪些人的活动不可以记载?我脑中所有关于“美术史”的知识都是从学院经典教科收书中获得的,其中没有成都地区的地域“样式”。为此阅读了许多我国近现代文史资料、各类著名人物传记,尤其是关于四川辛亥革命以来著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界人物的相关史料、传记,还到茶馆聊天“摆龙门阵”,到民间书画古玩市场闲逛,然后拟定了一长串 “访问”名单。成都美术志的资料收集编辑过程是一个学习四川近现代历史和寻访民间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前辈老师“请教”的过程,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公开发表的“议论”“观点”,听到了有的作品、事件后面发生的“故事”,看到了正版艺术史无法涉及到的个别“片断”……。《成都美术志》按照要求在出版前邀请成都美术界领导和部分画家、理论家先后进行了三次审读,值得欣慰的是在审读讨论期间,有关成都地域美术的话题在地方群体的互动对话中逐渐形成共识。
《成都美术志》是全国第一本现代地方断代美术志,重视全国现代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大背景”,同时追溯一座在我国中心大同文化里的地域城市艺术发展脉络
《成都美术志》是全国第一本现代地方断代美术志,记录1840年至1999年发生在成都的美术现象,期间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美术活动包纳近代、现代、当代艺术创作,因为资料文献的局限性,全书记录的资料偏重于20世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晚清绘画状况不够详实。20世纪是一个大革命时代,各种社会革命运动、新文化革新思潮风起云涌,“美术”因为它图像意义和创作方式具有个体化的自由空间,在20世纪被一批志立于改革社会的年轻人推到了革命运动、革新思潮的风口浪尖上,或为政党、集团文化宣传工具,或为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渲泄手段、工具,由此20世纪的中国美术因为20世纪的风风雨雨的社会革命表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敏感、活跃。这一时期,成都对外空前开放。从晚清、民国初年的留学热潮至今一百多年来,成都人、尤其是成都的青年人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积极地向外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心城市)、外国学习先进的新兴的革命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20世纪一百年来发生在北京、上海和沿海地区、江浙一带等地的新思潮运动常常很快地在成都地区有所表现。近百年来,成都艺术家们一直在虚心地深刻地反省本土的“封闭”“滞后”,热烈地向往“中心”“外出”,而成都平原的历史地理环境相对沿海城市、中原中心文化城市不同的“观念”“风俗”“方式”,也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本土“经验”塑造艺术家们的本土“身份”。
《成都美术志》在资料收集方面注重了两个方面的材料,一个方面是全国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包括1950年以后新中国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对成都美术的影响,一个方面是由这些影响形成的各种“现象”,现象相互之间上下文联系以及现象“关系”的发展变化。《成都美术志》重视全国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大背景”,同时追溯一座在我国中心大同文化里的地域城市艺术发展脉络,中国内陆特色的地方美术面貌。如果说“志”书的功能为客观地记录历史、见证历史,那么《成都美术志》所记录、见证的是中国西南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城市的艺术家们 “出蜀”“入蜀”“出国”“回国”,在20世纪大革命时代不断走向开放的历史,和在“开放”中不断对外“交流”“碰撞”、对内“革新”,寻找自我方位、自我状态、自我个性风格的历史。
晚清以后逐渐复兴的成都平原文化带有移民文化色彩,从中滋生出比较缺乏历史承继的向外积极吸纳的兼收包容活力
20世纪末,外地一些艺术批评家评论成都市为现代艺术、先锋艺术活动的“重镇”。《成都美术志》所记录的史料没有提供太多的所谓“重镇”个案,事实求是地展示了地域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元代以后到清代几百多年,成都平原失去了汉代主流城镇和唐宋时期“杨一益二”的辉煌,全国书画艺术创作活跃的中心地方为东南江浙地区和中原的首都北京市。《成都美术志》“概述”的第一段简单地叙述了成都平原蜀地晚清以前几千年美术发展的纲要,其中提到:“元、明、清以来,由于战争的破坏,成都平原经济衰退,绘画活动逐渐萧条。”晚清至民国初年,四川盆地文化全面复兴的社会基础除了全国民主主义社会革新运动的大背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问题,就是1713年到1851年,清朝政府谕令四川“滋生人口” ,向已经荒败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四川盆地大规模移民,晚清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多逐渐兴起的四川文化与本土汉、唐、宋的传统历史文脉相对断裂,带有新生的年轻的移民文化色彩,从中滋生出比较缺乏历史承继的向外积极吸纳的兼收包容活力。“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一直是成都现代美术创作的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现象。
20世纪初,成都美术界有意义的现象主要为学习西方模式的学校美术教育,而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活动。美术志“国画”一节中记载了一些在成都平原的四川晚清著名国画家,这些人一般崇尚古意,以追求宋、元、明代大家为品格上乘,没有较大的社会文化影响,缺乏延续性创造发展传统艺术精神的表现力。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的著名画家,如任伯年、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高剑父、陈树人、王一亭、齐白石等人的绘画活动十分活跃,在早期国内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中,在新美术活动中,从传统到现代之间承上启上,开拓新风。这些人的艺术创作除了全国现代美术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外,从地域文化方面,对于所在区域地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入。至今21世纪初,杭州市许多青年画家常常会自毫地告诉外省人,他们可以在学院教材以外的民间社会中看到晚清以来著名大家绘画原作,优秀作品的原作赏习和著名艺术家亲身师徒传授经验对于年轻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成都美术志》与历史上一些关于西蜀绘画文献史书相比较增加了一个特别内容,就是根据20世纪美术活动特点,专门设立了教育专章,用了一定的篇幅记录20世纪初成都早期的美术教育史实。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就设立了手工图画专修科,到1924年四川美术专门学校成立,创办艺术学校、艺术社团,走出达官贵人的小茶座和文人雅士的书斋楼阁,到公共社区举办绘画作品展览会,已成为时尚。当时,学校里教授绘画的老师大都为留学日本、法国、比利时和到上海艺术学校学习美术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讲座、报刊专栏、学校教学和艺术展览会积极倡导中西艺术文化交流和美术革新,大力宣传西方美术思潮,西方绘画原理,主张以美术、美育启蒙社会、改造社会。各美专学校和各院校艺术系的师生写生团、写生队活动,学校师生中西作品联合展览会常常轰动一时,成为新闻界、文化界舆论焦点。1933年由成都文化界一批德高望重“五老七贤”前辈们组织成立了书画社《蓉社》,该社以增进文化、保存国粹、研究艺术为活动宗旨,像这样的扶持国粹传统文化的社团满腔热情地积极支持随黄宾虹入蜀定居成都的“大走客”吴一峰的旅游写生创作,支持学校美育教育。成都美术就这样在出蜀到外地、国外学习的年国轻留学生的革新活动和西方模式学院教育的影响下开始复兴,当时学校里所教授的西方式的绘画思想、技术、原理,还有外地特别是上海新美术活动对成都画界的吸引力很大。当然,当时除少数到外地、外国学习的人以外,成都本土年轻人都是通过一些较粗糙的印刷品接触到外地和国外著名艺术家的优秀美术作品。这个历史事实对于认识理解20世纪一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成都当代美术发展十分重要。
《成都美术志》作为一部综合表现成都地区各美术种类发展的史志,在全书篇章叙述上不强调“现代”“当代”与“传统”的区别,但关注变化
成都美术志》作为一部综合表现成都地区各美术种类发展的史志,在全书篇章叙述上不强调“现代”“当代”与“传统”的区别,但关注变化,注重收录不同画种内部的发展演变和发展高峰期典型案例。
20世纪初,因为物质经济条件,油画颜料缺乏,油画在成都并不活跃,抗战以前展览会上的“西画”更多的是水彩画,抗战期间油画展览主要为外地入川艺术家的作品。《成都美术志》关于早期成都油画情况的记载不多,图像资料就更少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后,全国院系调整,成都画家大都集中到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成都油画界仅剩下几个负责布置重大政治活动集会会场的油画工作人员。然而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成都油画影响显著,其声名享誉国内外。《成都美术志》写作过程中注意了这一变化过程脉络的疏理,不重视有关“观念”理论“原则性”的讨论。显然其发展变化现象与早期油画发展滞后有关,很难想像如果不是20世纪40年代后四川较有影响的油画家刘艺斯、刘国框、刘一层等人的创作由于其自身浓厚的地域乡土气息,不可能在当时得到认真研究和宣传;如果不是当年四川美院油画系教师队伍中没有一批像中央美术学院那样的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油画大家;如果不是四川美术学院院址在重庆黄角坪,那里的学生因此会有那么多的自由去研究阅读各种国内外画册,学习他们喜爱的艺术和发表他们自已想说的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川一批青年艺术家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力度去突破主流画风和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敏感的话题。而20世纪90年代后,因为在70年代末就受到美国具象绘画影响,自由发展起来四川油画乡土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绘画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条件逐渐转换为当代新具像绘画,继而从新具像开始进一步拓展开来,成为中国当代油画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内外关注。
成都雕塑的发展与成都油画有一些相似处。民国时期成都学校雕塑教育差,刘开渠的室外抗日塑像活动更多地为社会影响,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的学院雕塑教育开始发展。由于地处边缘,缺乏充足的学习欧洲式学院雕塑的条件,四川雕塑艺术因此具备了与民族民间艺术合作的能力。《成都美术志》“雕塑”一节用了较大的篇幅记录大邑县《收租院》泥塑创作情况和的当年的历史文化背景,编辑写作时正遇到有关《收租院》著作权的争议风波,特别对《收租院》泥塑创作的史料完全重新做了认真的调查考证,希望《成都美术志》以方志的科学性反映真实的历史事实。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部分师生应邀到大邑县,和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美工、当地民间艺人合作,地主庄园陈列馆现场完成了一组96米长,由114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人物组成的泥塑群雕《收租院》。该泥塑群雕塑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典型意义和情节化的表现叙述方式,以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与西方学院艺术的和谐结合,成为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其实成都地区一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意义的雕塑活动都不太活跃,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在1965年以前为陈列宣传内容所做的系列造像活动还是民间留传下来的与寺庙泥塑差不多的本土传统形式。四川美院部分雕塑系师生进入大邑县安仁镇是一个划时代的合作 “行为”,师生们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情和当地政府领导以及民间艺人对学院老师造型技术的认同尊重都一样地饱满自信,他们的积极互动产生了中国本土里程碑意义的现代雕塑,也激活了成都地区现代雕塑创作局面。《收租院》泥塑群雕创作一直影响到以后的成都雕塑发展,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的城市雕塑。朱成、邓乐等人的架上雕塑创作,对于不同材料、不同制作方式、不同创作思想的兼容能力和由此产生的独特风格,以及21世纪的成都公共艺术活动等都与《收租院》现象有本土脉络联系。
成都画家中国画家最多,《成都美术志》记录国画的发展情况和国画家简历的篇幅也最多。还在做成都国画前期资料收集工作时,就有一些人提醒注意成都国画界老前辈们的创作,成都人常常 十分感概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没有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推广平台。根据《成都美术志》所收集到的史料来看,因元代以后的历史局限性,成都国画在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复兴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就带着它自身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国画晚清的资料主要摘录于几本蜀地绘画史稿,我们能够阅读到的原作不多。民国初年,成都较活跃的国画家大都在美术学校里任教,这些人倡导新美术思潮,其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学院西画画理,有的甚至擅长中西技术结合。成都书法与成都国画虽然都为成都的传统国粹,但前者在19世纪中叶后因何绍基、张之洞先后出任四川学政,振兴蜀地文化。书法随四川学界的生气开始欣荣,发展到民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成熟的作者,成都本土文化中积极的传统文化底气主要由一批学者的努力保留在成都书法创作中,致使成都书法有能力延续传统精神发展至今,形成自身地域特色。而国画在晚清处于滞后,民国初年受到学校美术教育和一批留学国外和到上海学习的年轻人新艺术思想的强烈冲击,与本土前辈画家相对断裂。其实成都国画从20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新思潮样式的 “新国画”的趋势,但这个“新国画”趋向因为地处非中心文化地区,发展不太稳定,其中有关现象长期缺乏系统的清理,研究阐释的理论也一直有点混乱。《成都美术志》根据时间历史顺序叙述国画发展脉络,在史料整理上不刻意清理“混乱”,但尽最大的可能性追求严肃的客观性。在编辑 “国画”一节的90年代部分时,《成都美术志》基本上以编年记录方式一一表现众多画家多元化的系列创作活动,甚至还记录了一些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其目的是希望较全面地提供文献,以方便后人做进一步清理,就有关地域性“新”的话题做深入研究。
年画在20世纪中、下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积极扶植,曾经担任了振兴大众艺术文化责任成为主流画种,《成都美术志》在四川美术出版社前辈领导的帮助指导下,较完整地记录了50年代至90年代以成都地区为中心的四川年画创作面貌。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四川年画的“黄金时代,当时四川人民出版社有关年画的年出版发行量高达100多幅7000万张,占同时期全国年画每年总发行量的七分之一。1984年四川8位年画家合作创作的9大元帅图《敬爱的元帅》荣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金奖、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一等奖的。这套9幅系列新年画组画借鉴了绵竹民间门画的表现手法,当时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正漾溢着一派现代艺术复兴气息,能够兼容现代与传统创作方式,采用“旧”时乡土气浓郁的门画形式画革命领袖像,创作出优秀的现代年画的画家可能只有四川人了。展览会的评委专家们经过一番争议后对该作品颁发了大奖,而广大民众却毫无异议地充满热情,四川人民出版社连续再版《敬爱的元帅》19次,累计发行1亿张,创50年代以来全国年画作品发行量最高纪录。
因为政府修志篇章结 构的要求,《成都美术志》没有设置专章反映20世纪末在成都各大街小巷表现十分活跃的行为艺术,这些活动资料主要列入到 “大事记”中。成都早期从事行为艺术的艺术家大都有过学习创作油画的经历,成都油画当代创作活动和在国际交流平台上所获取的新观念、新信息无疑促成了一部分艺术家对行为艺术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7年内,在成都市区各街头巷尾和公共社区进行的行为艺术活动和其他多媒体艺术多达100次以上。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的一些新锐观念、实验形式就这样在街头、酒吧、社区广场、旧仓库、老房子里逐渐向休闲、平和、好风雅的成都市民传播,并随着市民好奇热情迅速升级为公共媒体的文化关注焦点。这个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成都都市公共社会文化意义大于一些外地评论家和文化精英们关于成都“先锋” “前卫”艺术城镇的研究。
《成都美术志》在文献方面的意义
《成都美术志》在文献方面对于全国美术史有一个意义,就是较系统全面地收集整理了1938年至1945年成都抗战时期的美术活动资料。以前,全国有关民国美术史的史书和论文在抗日美术方面很少提及到成都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美术一般以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市的活动为主流,成都、昆明、桂林情况史书记载都比较零散。其实当时成都市为抗战后方的一个主要的大城市,文化艺术和学校教育都十分活跃,尤其书画市场比其他后方城市红火热闹,带动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画金石展览,居住后方各城市的美术家大部分都要到成都办展览买画,也因此促进了成都的美术社团活动和美术创作、美术评论。《成都美术志》记录了当时举办的各种类型展览会;一批外地入川著名艺术家在成都的活动,特别是国画家张大千、书法家谢无量、雕塑家刘开渠、工艺美术家李有行的创作;成都抗战美术刊物情况,《新艺》月刊、《自由画报》出版编辑活动;张漾兮、谢趣生这两位本土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蓉社、蜀艺社、四川美协、四川漫画社、中华艺社、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战协会成都分会等一些社会团体活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南虹高级艺术职业学校等一些学校艺术教育情况,包括早期著名工艺美术家在成都进行的工艺美术教育;成都市区室外人物纪念塑像活动,抗日无名英雄像和川军抗日牺牲将领塑像活动等……。抗日战争时期对于中国美术是一个以民族爱国精神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高潮期,美术作品以通俗易懂的图像形式成为抗战建国、爱国、救国的重要宣传工具。《成都美术志》收录的资料提供了抗战后方一个位于国民政府政治中心之外的城市美术宣传、美术创作史料。这些史料与当时的重庆市相比,带有更多的社会公共性、大众文化性和艺术家自由创作的个性。
《成都美术志》是一本现代艺术文献书籍,编辑过程中毫无疑问地十分注意学习现代方志学和现代年鉴学写作方法。除了按照志书写作要求,所录入记载的史事资料不带主观倾向叙述,语言文字为文件格式外,在 “直书”史事中,还有意识地努力追求现代意义的科学性、理性分析性,突出文件的文献信息,有的篇章概述内容直接采用较精确的百分比数字统计来表述。全书刊登了300多张图片,图片内容不以艺术家创作作品为主,其中相当部分根据文字内容需要为文史性资料图片。附录的最后的一章“历年美术展览活动一览” 化费了许多精力,做得十分辛苦,全章按照历史时间顺序记载了民国8年(1919年)至1999年成都市区20世纪80年来各陈列馆、展览馆、美术馆和各街头、公共社区举办的主要的绘画展、书法展、篆刻展、雕塑展以及各种新媒体展览。作为《成都美术志》的结尾篇,我非常希望“历年美术展览活动一览”能够以现代文献写作方式展示出它的信息价值:20世纪对于中国美术界来说是一个展览的时代,许多重要的美术现象、美术作品都产生在展览会上,研究20世纪美术现象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美术展览。一个又一个的美术作品展览会不断地影响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创造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当然也创造了成都现代美术。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