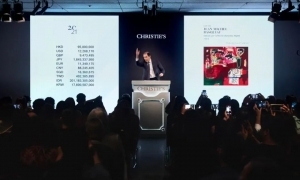坐落于普罗旺斯艾克斯的塞尚雕像。
©2025塞尚年
在面对大师时,我们需要超越“瞻仰”的惯性视角,去直面更具挑战性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身在艾克斯时,总以为他乡更好;而今身在他乡,却又思念艾克斯。只要你出生于此,便再无其他愿望,因为没有什么地方能与之媲美。
——保罗·塞尚

塞尚位于艾克斯的莱斯劳维斯画室
这座画室于1901年由艺术家亲自设计建造,是塞尚的最后一处创作空间。如今,画室在持续修复的同时,也向公众敞开大门。
©Office de Tourisme d'Aix-en-Provence Atelier des Lauves
罗马人于公元前122年建立了温泉之城艾克斯-普罗旺斯,这里也是伟大的画家保罗·塞尚的家乡。颇具讽刺的是,塞尚去世时,该市格拉内博物馆那位排斥其作品的馆长曾宣称,该馆将永不展出这位艺术家的任何画作。但时过境迁,如今的格拉内博物馆收藏了十几件塞尚的作品,其中包括一幅在当地皮戈内酒店花园中创作的风景画。

比贝米斯采石场,在1890年至1904年间,这里是塞尚的创作乐园,他于嶙峋的岩石与雄伟壮丽的圣维克多山之间,锤炼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Office de Tourisme d'Aix-en-Provence Carrières de Bibémus
现在,这座城市正以“塞尚年”这个活动全面拥抱这位曾经被她拒绝的儿子。这次展览的规模远超一次常规的大师回顾展,是由一系列深度学术研讨、城市级公共艺术项目与跨领域文化对话的集合体。然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周年纪念或文化朝圣,它更像是一次主动的“重新激活”,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图像以秒速生产与消费、观念艺术早已成为主流的今天,保罗·塞尚那种近乎“笨拙”、执拗的观看与建造方式,对于当下的艺术家和每一个试图通过图像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莱斯劳维斯画室是塞尚生命最后使用的画室,它坐落于艾克斯市中心以北,可将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视野绝佳。摄影:Sophie Spiteri
塞尚留给后世的“创作工具箱”
1839年保罗·塞尚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23岁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前往巴黎学习绘画。在巴黎,塞尚认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毕沙罗对年轻的塞尚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曾一起在户外写生,创作风景画。塞尚以独特的视角,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可以由圆柱体、球体和锥体构成。同时,他也认为绘画并非盲目复制现实,而是寻求各种关系的和谐。

保罗·塞尚,《雅德布法的房屋和农场》(Maison et ferme du Jas de Bouffan)(局部),1885-1887年,布面油画,60.8 × 73.8 cm,布拉格国家美术馆,捷克共和国 © 2023 布拉格国家美术馆 ©2025塞尚年
2025年,“塞尚年”穿越式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亲身走进塞尚“画室”的机会,在“看”他创作的同时,也让我们得以深刻感知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世提供了一套可以轻易模仿的风格范式,而在于他揭示了一种关于“如何观看”和“如何建造画面”的方法。
永恒的“建造”
当印象派在追逐流光掠影,试图捕捉特定时刻下的大气与观感时,塞尚从中抽身,他要的不是“瞬间”,而是“永恒”。
他背对浮华的巴黎,面向沉静的圣维克多山,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耐心,探寻事物表象之下那不变的内在秩序与几何结构。这种对永恒的建造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立体主义的诞生。

保罗·塞尚,《圣维克多山》(La Montagne Sainte-Victoire,1897年),是塞尚毕生创作的约80幅同题材作品之一,现藏于伯尔尼美术馆。
塞尚的每一个笔触,首要任务并非模拟光影或附着色彩,而是作为一种结构单元,参与到整个画面的“建造”之中。它们相互平行、倾斜、叠加,形成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构造。
这是一种将绘画行为转化为思维过程的实践,也或许是塞尚留给后世艺术家最直接、最具操作性的遗产。

保罗·塞尚,《森林》(Forest,1890年),布面油画,72 × 92 cm
“慢”与“拙”的当代价值
塞尚曾说自己进步得非常缓慢,因为自然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向他显现。但这种沉静、专注的创作状态,鼓励着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以看似缓慢却坚定的方式重构画面秩序。这种秩序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画面建造所实现的。

保罗·塞尚,《一篮苹果》(Basket of Apples,1895年),布面油画,62 × 79 cm

保罗·塞尚,《玩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1890 - 1892),布面油画,135.3 × 181.9 cm
乔治·莫兰迪早期的作品明显受到塞尚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形状的描绘和透视法的运用上。莫兰迪毕生描绘瓶瓶罐罐,但他并非在乎物的形态,而是在探索物与物之间、物与空间之间的永恒秩序,这正是塞尚“感知的秩序”在20世纪中叶的回响。

乔治·莫兰迪,《静物》,1943年

乔治·莫兰迪,《静物》,1919年
对“物”的反复描摹也体现在塞尚对圣维克多山的创作中。他将一座具体的山,转化成一个关于观看、结构与精神性的图腾。在处理“风景”与“地方”的关系时,不再以“再现”为目的,而是转向探索人与特定场域之间的深层链接,即如何将一个物理空间,转化为一个精神性的、被重新“建造”的场域。

保罗·塞尚,《圣维克多山》(Mont Sainte-Victoire,1895年),布面油画,73 × 92 cm

保罗·塞尚,《比贝米斯采石场》(Bibemus Quarry,1900年),布面油画,65 × 81 cm
对“物性”的极致尊重
通过成百上千次的描绘,塞尚将日常静物从传统绘画的附属与象征角色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前所未有的物质存在感与尊严。这种对“物性”的极致尊重,深刻影响了意大利的“贫穷艺术”、日本的“物派”,以及当代装置艺术中对“特定对象”的哲学性探讨。

保罗·塞尚,《苹果与饼干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apples and biscuits,1877年),布面油画,38 × 55 cm
对“物性”的终极强调是塞尚艺术思想的一个核心,也是他之所以被誉为“现代艺术之父”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是一种绘画技巧,更是一种深刻的哲学观念,甚至改变了西方艺术的走向。

保罗·塞尚,《桌上的花瓶》(Flower pot at a table,1869年),布面油画
古典或学院派绘画追求逼真的三维幻觉,并常常让物体服务于某个宗教、神话故事或道德寓意。苹果可能象征着诱惑,酒瓶可能暗示着狂欢……塞尚剥离了这些文学性和象征意义,他画的苹果就只是一个苹果,一个具有特定重量、体积和色彩的纯粹物体;它们不再仅仅是“被描绘之物”,而是拥有自己的体积、密度和沉默意志的“存在者”。

保罗·塞尚,《七颗苹果的静物》(Still life with seven apples,1878年),布面油画,17 × 36 cm
塞尚作画极其缓慢、反复修改,过程充满挣扎,这也体现了他对“物性”的尊重和探索的艰难。他不是在轻松地“描绘”,而是在与对象进行一场艰苦的对话,试图通过画布上的每一次笔触,去实现那个独立存在的物体的真实性。

保罗·塞尚,《法兰西岛的风景》(Landscape in the Ile de France,1865年),布面油画,33 × 41 cm
怀疑、坚忍与艺术的独立性
超前的思维常常得不到理解和接纳,开拓者注定要忍受孤独和痛苦。很多天才如此,塞尚亦如此。

保罗·塞尚,《手持调色板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Palette,1890年),布面油画,92 × 73 cm
在塞尚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面对的是公众的漠视和评论界的批评。他的画被嘲笑为“粗俗”、“半成品”……他在主流艺术圈中长期被边缘化。

保罗·塞尚,《自画像》(Self-portrait,1882)
最终,他选择离开喧嚣的巴黎,退回到在艾克斯的老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回归,更是心灵上的主动隔绝。在艾克斯,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创作自己的艺术,可以日复一日地面对圣维克多山和那些平凡的苹果与陶罐,可以毫无顾虑地直面艺术的本质问题。

保罗·塞尚,《平原之河》(River in the plain,1868年),布面油画
在绝对的真诚中怀疑一切,在无尽的孤独中坚守阵地。这一精神也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另一位艺术大师——贾科梅蒂。
贾科梅蒂曾言塞尚是他唯一的老师。 但这位老师教给他的,不是技巧,而是态度。观看贾科梅蒂的雕塑,尤其是《行走的人 I》(Walking Man I, 1960年),我们能感到一种被反复剥削、压缩至极限的存在感。那细长、崎岖、仿佛在空间中被灼烧过的形体,是艺术家无数次增添又削减、肯定又否定的产物。这与塞尚面对苹果时的状态何其相似。《行走的人》不仅是一个在行走的人,更是“行走”这一行为本身,以及艺术家在试图捕捉“真实”时那痛苦而坚忍的挣扎过程的物质化身。它以一种悲剧性的崇高,彰显了塞尚所代表的那种艺术独立性——艺术无关乎取悦市场,而是一场艺术家与存在真相之间的终极对话。

贾科梅蒂,《行走的人 I》(Walking Man I, 1960年)
对于很多后世艺术家而言,塞尚都如同他终其一生描绘的圣维克多山,既是横亘眼前、令人敬畏的挑战,也是一座可以时时回望、用以校准方向的标尺。艺术的本质永远关乎创作者如何以其独一无二的感知,为我们身处的世界,建立一个坚实、真诚且充满生命力的视觉参照。2025年,当我们回到塞尚的“画室”,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无数条通往未来的道路的起点。正因如此,塞尚,永远是当代的。

《加尔达纳(横向构图)》(Gardanne (Horizontal View),1885年),布面油画,65 × 100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