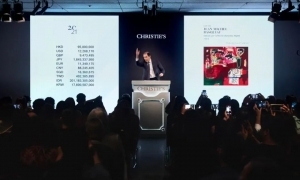蓝庆伟:大家好!我是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蓝庆伟,是本次论坛下半场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开始“新绘画及其边界”讨论会的下午场。下面我将讨论下半场的议程介绍一下,下午将进行8位艺术家的主题发言。他们分别是杭州的余旭鸿、李青、薛峰、陈彧君;西安的王风华;南京的陈辉、包忠;北京的张小涛;讨论会最后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杭春晓博士为本次论坛做总结发言。首先进行发言的是杭州的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创作有着相似性,即把绘画当成是一种新媒体、开放的空间来思考自己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分析性”,这种分析性包括观念的逻辑和对现实问题的认知方式。他们从身边的、现实的、社会的问题出发,朝着观念的方向去引申。下面有请第一位发言人余旭鸿,余旭鸿现任教于中国美院油画系,他在作品中十分关注“光”与“影”之间的关系,并做了大量的实验,而在他08年博士论文《绘画与光影》中更是做出了详尽的理论基础研究。
余旭鸿:我今天讲述一下自己对绘画的理解和考察,对于今天的论题“新绘画及其边界”,我将谈一谈对新绘画概念的拓展。我们为什么能看见物体?这一问题的最初提出可追溯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 。光学(optics)与视觉(optic)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根,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史学家已认定,早在公元前400多年中国的春秋时期,墨子就观察到小孔成像的具体现象。17世纪,开普勒经过光学与医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视觉具有与照相机同样的功能。眼睛的瞳孔就像照相机暗箱的针孔一样,进来的光被晶状体液所聚焦。,在视网膜上形成了一个倒着的图像。
绘画如何呈现所见之物?如何把我们看到的事物转换成二维画面的视觉呈现?透视法与明暗法是西方绘画呈现三维现实的幻觉的主要手段,光学与暗箱的研究则是它的两个拐杖。依据光影科学引发的视觉追问,绘画如何呈现所见之物这一线索,从布鲁内莱斯基的线性透视法到阿尔贝蒂的“视窗理论”,以及丢勒版画中的透视法视觉呈现,透视法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视法的发现,透视只能表现往后退的效果,不能表现往前凸起的效果,所以达芬奇花毕生精力研究如何凸起的效果,这就是浮雕感。
纵观西方绘画史,我们发现乔托的壁画并不是非常写实,但在100年后的画家竟奇迹般地开始用照相机般的准确度来作画。为什么画家的写实能力突然增强?大卫·霍克尼(Hockney David)在《秘密的知识:古代大师的失传密技》(Secret Knowledge——Rediscovering the lost techniques of the Old Masters )一书中研究了1420—1430年间欧洲现实主义风格骤然兴盛、写实能力突然大增的原因,全面研究诸如暗箱之类的设备被画家们作为绘画工具使用,说明新技术对绘画的影响。这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对于大多数理论家研究而言,绘画跟科学和技术手段之间的联系通常被忽视。
为什么在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人》篮筐中的面包有模糊的光晕?我们在正常看物体时并不会出现这种效果。英国学者菲利普.史蒂曼教授(Philip Steadman )历时30年的研究写就了《维米尔的暗箱》(Vermeer’s Camera ),并在BBC的摄影棚中重置了一遍,对维米尔用暗箱技术来绘画的过程作了很具体的研究。
现在我们就易明了这是镜头没有聚焦的视觉效果,他用小光点来呈现眼之所见。基于绘画中对暗箱技术的尝试,使得维米尔的画有一种静谧的效果。在卡拉瓦乔《以马忤斯的晚餐》(Supper at Emmaus1596-8至1601年)一画中右边的圣彼得以及中间基督的有着明显透视的手臂。虽然我们认为卡拉瓦乔的画比较自然,但细看之下发现一些矛盾的地方:基督的右手和彼得的手的尺寸是一样的,然而在我们看来,他的手本该更接近观众,也本该更大。而圣彼得的右手比左手更大,但是左手更接近观众。为什么圣彼得的右手比左手大呢?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记录和绘画实践的考察,业已证明有许多画家在利用暗箱原理这一技术性观视来协助绘画。暗箱为画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以及再现物质世界的方法和更快捷、更有力的制作图像的新工具,也拓展了绘画的新领域,绘画的整个历史也受到了光影科学和视觉原理的影响。
从小孔成像到“暗箱”的发明,将现实“如实地”记录在二维平面上的期许,在摄影中淋漓尽致地还原了。摄影是科学与艺术的胎儿,它是暗箱的变种。摄影(photograph)一词意为“光之书写”,“photo”原意为“光”,而“graph”原意为“描绘”,但这种“光之书写”首先将世界的“光影“颠倒,在底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现实事物矛盾的景象。摄影术最初的原理和暗箱原理如出一辙,其实并不是说摄影术替代了绘画,相反,绘画在某种程度上支撑了摄影术。有人坚持绘画有独特的价值,新技术很快融入到了绘画里面,但也有人认为绘画已经死亡。
其实,当代艺术中的摄影和移动影像媒介的媒介技术进步论并不真实也立不住脚:在摄像机发明之前其实就有了可移动的彩色图像。有人在1290年就用暗箱来呈现“移动影像”。 600年前绘画业已实践了现代影像艺术的技艺与观念,并且这些技术的发明大多源于绘画实践。
丢勒把三维的现实转换为二维的平面,与后来的立体派是有某种联系,我们现在的绘画大都还在使用明暗造型,但我们很容易忽视光影的象征性意义,比尔维奥拉的光影作品中有很强的隐喻性,现在的图像时代用光影建构了一个虚构的现场,而这个现场最大的问题是费尔巴哈提出的“重图像胜于事物,重复制品胜于原作,重表现胜于事实,重现象胜于存在”。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视觉经验技术化,视觉经验技术化和世界图像化背后最大的因素是高度发达的技术。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研究绘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注个人经验之外的普遍性意义,风格的差异只是个表层,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的差异与共通性的东西,我觉得新绘画不仅是对外延的拓展,只是跨媒介、跨学科,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对绘画的本体研究有很多缺失。
蓝庆伟:他从光影的研究到达盖尔摄影术的发明进行了陈述,我的问题是光影的理论研究对今天新绘画的意义,请您再简单地谈一下。
余旭鸿:我主要谈三点内容,第一是绘画的形而上意义,本雅明在其著名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摄影的可复制性破坏了艺术作品的灵韵(Aura)。 一幅油画是独一无二的,而一张画的照片的底片却可以冲洗出许多一模一样的照片,对其原作的唯一性和笼罩于其上的“灵韵”构成了挑战。现在绘画的问题不是摄影破坏了灵韵,而是作品中本来就没有灵韵,只有苍白的图式,抑或是个人风格化的注册商标。这种苍白的病症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画家本身思想的堕落、无病呻吟,不再对世界敬畏,浅尝辄止。绘画日益沦为商品,变为利益链中的批量生产的产品,怎能具有人性的光芒?另一方面是宗教的式微,社会日益世俗化。商业全球化致使世界扁平化,图像的消费化致使思想的肤浅代替思考、平面代替深度的娱乐化。绘画的起源之初,光影就有形而上的价值,超越了物质的实在。在伦勃朗的摇曳的烛光中,我们能体验到穿越时空的神性和人性的光芒。即便在丢勒利用“阿尔贝蒂之窗”来描绘所见之物,背后仍旧有对世界的敬畏和迷茫。光影原初的形而上意义或许是抵抗图像时代苍白光影的出路。
第二点是提供一种新的视觉经验绘画在图像时代之前已经“死”了两次。一次是在1620年代。暗箱的出现使荷兰外交官和诗人康斯坦丁 .惠更斯发出了绘画已经死亡的感叹,认为这是“巫术”。但他在看了利用暗箱创作的绘画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强调绘画没有死亡,这个新装置可以使其革命化。第二次是在1839年。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见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术后,他发出了著名的断言:“从今天起,油画死了!”。 但绘画并没有死,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
现在,图像的日益增殖、新媒体艺术的强势渗透,绘画再一次面临死亡。但是,像绘画这样的“图像”还有其特殊的价值。移动图像转瞬即逝难以具备绘画的魅力。我们应该反观绘画自身,去实现康斯泰布尔的绘画理想:“从飞逝的时间中截取片段,赋予它永久而清晰的存在。”事实上,暗箱为凡爱克、卡拉瓦乔、维米尔等画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法,他们的作品也已呈现了一种新的视觉经验而耐人寻味。摄影也为印象派画家提供了绘画的另一种可能。现在各种图像也可能同样如此,如果绘画呈现了一种新的视觉经验,那么图像时代也是绘画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之机。
第三点是反映时代的生存体验如果画家只关心画面的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害处,但事实上,画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面对的不只是艺术自身的问题,他们活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对这个世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便是图像的千变万化,我们对这个世界皆有体验。“太阳底下无新事”,压抑与希翼、苦难与欢愉、宁静与高扬、人性之善恶等等都与先前无异。只有重视我们的体验才能对抗图像肤浅,在图像的背后亦应关注生存体验。
为什么我们在看“汶川大地震”光影闪动的影像时会掩面而泣心如刀割?当代画家应多关注当下视觉文化现实和社会问题,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并把在生活困境中的内心体验通过个人的方式呈现出来,作品是与当下现实、人与人、社会、自然、历史活生生的联系,是个人需要的外化,同时是社会群体生存感觉的缩影,逐渐达到私密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作品像一滴水,来源于世界,却又折射出整个世界;作品也像暗箱中的投影,来源于外部世界的光影,只是要经过一个小孔罢了。
蓝庆伟:余旭鸿从光影的研究到达盖尔摄影术的发明进行了陈述,我的问题是光影的理论研究对今天新绘画的意义,请您再简单地谈一下。
余旭鸿: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我们要“脚踩两只船”,意思就是警惕一种彻底性,邱志杰给黄永砯写的最早介绍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警惕一种彻底性,这也是当代绘画的一个问题,你在关注当代发展的时候,不能割裂与过去的联系,不是说你彻底颠覆过去,弑父情节是不理智的。传统绘画在当代的延伸,应该是我们更关注的命题,尤其在当代艺术形式纷杂,但缺乏一种共同的判断价值。讨论光影的问题,第一是对我个人创作会有一种参考,第二是直指新绘画,新绘画其实是指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在是一个图像泛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绘画有什么价值?只有在绘画的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建构一个理论框架,如果是真正有理想的艺术家,他是在跟时代交流,跨时空交流。
郝青松:这次论坛其实涉及到了对我们自身历史的一个考察,新绘画的概念应该是在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提出的,《艺术当代》也做个这样一个专题来讨论这个概念。在西方出现的新表现、新精神等艺术流派,无疑启发了我们对新绘画概念的命名,但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在西方命名的“表现”、“精神”等词汇更接近对艺术本质的阐述,而我们却使用了“绘画”这样一个只是表达艺术门类差别的词汇。这说明,我们自身历史中有着很浓重的绘画情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在探寻西方的绘画究竟是什么?即便在今天以观念表达为中心的艺术时代,绘画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目中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载体。无论如何,新绘画的出现已经是客观的现实,虽然它的命名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联系到我们的历史来探讨新绘画的概念和意义,我们就能理解余旭鸿努力对西方绘画做出的知识性研究的价值所在,也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对新绘画的未来做出判断。
蓝庆伟:李青的《大家一起来找茬》系列广为大家熟悉,这种来自经典的训练视觉反映游戏使绘画有了新的可能性,并在经验与超验、形式与观念、游戏与规则之间的对立性中走向了稳定与成熟。李青将从《大家来找茬》系列讲起,一直谈到今天的创作,下面我们欢迎李青发言。
李青:下面我介绍一下05年至08年的作品,这张是我临摹的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弗里德里希的一张作品,旁边我又画了一张小的,把里面的主人公置换成了我自己,展览时两张前后放置,产生一种透视上的错觉,感觉是一样大的,通过这种空间上的关系来勾起观看者对于时间的联想,画面中的人背对着观者,面向雾海,面对一片虚空,从古代到现在,人类最致命的问题是人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的虚无感,这个作品放在开篇说明了我的艺术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用智性的艺术方式去重构一种多重的时间和空间,完成对个体生命的延展,缓解这种虚无感给人的压力,一般来讲,在宗教中对这个问题会有它的解答,用对彼岸世界的虚构来缓解这种压力,我想艺术也可以有这种作用。我的绘画中成对的比较多,这组作品叫《局部同一的像--小丑与猫王》,左边是来自委拉斯贵支画中的小丑,右边是猫王的图片,对他们面部进行局部的粘合,所以一些五官的局部是同一的,画面上方英文题铭的意思分别为:“他们说我是小丑,但我是一位艺术家”、“他们说我是王,但我是一位艺术家”。在委拉斯贵支的时代,艺术家的地位和宫廷里的小丑差不多,现在的艺术家则被冠以猫王般的明星光环,这件作品讨论了艺术家的自我界定。《大家来找茬》系列开始于05年,当时在思考图像时代中绘画的可能性,试图从绘画的本质,即绘画的发生、生效的机制入手。通过游戏的方式诱导观众去找两张画之间不同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观众无法发现两个完全一样的地方,因为绘画是不可复制的,每一笔都会有偶然性,当观众开始关注笔触和风格,形象就被解构,这就把形象和绘画性离间了。这一系列会涉及到时间性,经历和回忆,真实和伪装,掩盖和揭露之间的重重关系。早期题材主要和青春叙事有关系,基本都是来源于自身周边的生活经验,比如我的自拍、与同学的合影、卡拉OK厅、还有年少时的回忆,后面的作品主题开始宽泛,因为我想要梳理一个作为整体的当代经验。有一种题材是会议、仪式等场景,很多来自媒体经验,这些看似重大的事件对个人的影响也许是空洞的,而用找茬的方式表现一种貌似重大的场合会更具戏谑性。我会在画中设置一些节外生枝的细节,比如茶杯位置的变化,花的开败等等,完成对宏大场面的解构。我觉得有时候用游戏化的方式故意地轻化沉重的现实,反而更能突出现实的分量。我的绘画比较强调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观众面对画的时候,实际上就像面对一面镜子,看到的是自己平时所忽略的潜在经验。“互毁而同一的像”系列,是把分别画的两张画,在没有干的情况下将画面黏合在一起再分开,两张画上的形象会相互融合,虚化,我会选择形象有相似性而意义上有差异或矛盾的图像。比如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的婚姻中互相塑造的关系;南京长江大桥和古城墙交织在一起,其实是两种政权的象征;墓碑系列中的碑文也会变得虚幻,墓碑主人的命运之间有对比的关系。在《交尾》这件作品中,当观众看到飞机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和政治、军事有关,但是我给出的题目是交尾,是对这种经验的否定和嘲弄。我也画一些单幅的作品来表现空间和时间上的悖论,这张作品叫《美丽岛》,中间是看似美丽的小岛,却被铁栅栏围了起来,观看者看似自由,但却被隔绝在外。这张作品用的是钱塘江潮水卷人事故的新闻照片,从画面风格看像一张江南风景,绘画表现事件的时候,会有一种风格化和冗余信息在里面。从“互毁而同一的像”系列往后发展,我把绘画行为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强化,产生了这件在乒乓球台上画地图,在颜料没有干的情况下打乒乓的行为,把两个图像打散,交换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对应现实中的关系,绘画处在了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最近的“软陷阱”系列中,乒乓球陷落在颜料塑造出的形象中,通过强化颜料的物质属性,使绘画和实物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蓝庆伟:谢谢李青的发言。下面请大家提问。
王春辰:看了李青的作品以及广州的、杭州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存在一个倾向,新绘画并不是说一个新的绘画出现了,而是在今天绘画语言的多元化中,如何用绘画去表达?去展示?艺术家在美术史的格局下的思考,每个时代每个人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所处的当下,我们怎么看绘画?或者说怎么看艺术?这一系列一体的问题,从李青的绘画里面看出他不仅仅在思考绘画,他把绘画作为一种手段,甚至涉及到装置上面,打破绘画的界限,来表达他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艺术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和理论家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们说一个艺术家画的好不好,要看技法、看感觉,今天的问题是中国建立了怎样的一种绘画体系?绘画的脉络?艺术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在历史上肯定存在一个上下文的联系,艺术家有意识地采用绘画的手段去表达自身的理解,告诉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他借用了很多历史的图像。当绘画与边界联系起来时,是有一种颠覆的关系在里面,不仅仅是对画面的要求,画面的背后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杭春晓:我做一下补充,春辰兄的观点带有消解绘画的倾向。李青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阐释和解读,那么他的作品是将绘画介入到装置中?还是把装置中的某些概念融入到绘画里?这是首先需要界定的问题。而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区分哪一类的作品可以放在绘画的范畴中讨论?对于行为因素介入到绘画的过程,这种表达最终落入到绘画中,才是对绘画边界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对于新绘画可能更有一种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把新绘画换化新艺术的概念,新绘画还是要有架上、有绘画这样的承载系统,对于这个系统,最终我们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拓展表达,并进而颠覆了我们习惯中对于绘画的理解,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称的上是新的绘画,而不是新艺术。
蓝庆伟:谢谢王老师和杭老师的精彩发言。下面发言的艺术家薛峰主要讨论的是对关键词的新形式的个人创作的思考。
薛峰:我先讲一下我的创作方式。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自己以前的绘画和今天对绘画的新认识对应起来,在这个自由交流论坛上,我想与大家讨论我想的一些方案草图,这个作品名字叫《上海后园》,我是宁波人,主要来往穿梭于长江三角洲一带,从我对这里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从中得出一个绘画表述的符号,“高速公路”是我进入到思考中的一个通道,它让我在两地之间发生物理关系,也因此在两点之间不断产生新的化学反应。我非常关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新闻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新闻,以及对网站最后一栏的社会新闻,可以说明前者是宏观的背景框架,有它的时代特征,后者是微观的被引起注意的个体行为,我用这样一种想法去梳理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谁都抓不住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征,我选择用一些碎片的方式来进行组合,这种组合是随机发生的,它们里面的元素之间是没有必然的上下文联系的,但是我认为它们被组合了以后有他存在的理由,我也从中去寻找另一种绘画的阅读方式,你看到的作品方案由很多独幅作品并置而成的,其中的方式有拼贴、剪切、手绘等,其实我是像建立一个视觉数据库一样去构筑的。至于如何阅读,这一点恰好能说明我在之前和现在的对读画方式的区别,之前的一幅画集中了所有的信息,现在把这种“集中”打破,并消解绘画的主题性,重新展开更具体的分析和局部的叙事方式,当你阅读它的时候,不用从指定的那一幅开始,就从你眼前的这幅开始。为什么是“上海”,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上海”这个词,是个地名,是个高处,是个目的地,是个出发地都有可能,是个发生关联的词。这个方案也是在挖掘自己的记忆做梳理。第一个方案是一个大背景的框架,延伸出信仰在物质发展中的衰退,教育在发挥社会功能中的滞后,环境的不可再生等。第二个方案是群体跟这个社会的联系,新的阶级矛盾在继续扩大。第三个方案是个人对身份的一种诉求,有关于自己的假象、想象和现实,通过我个人的感受把这种思考置身于多种环境中去说明。从社会状况到群体矛盾再到个体问题,通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去表达我个人对绘画思考的一种线索。我以前想通过一个系列的油画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后来发现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组《上海后园》方案的出现,是我在创造过程中的更高的需求,那么这种转换会不会有效?会不会空洞?我想接下来需要去做一些感性的呈现。
方志凌:薛峰是我在杭州的展览上认识的,油画画的非常好,现在对油画产生了怀疑,做了《上海后园》这一个方案。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情感的深度、思想的敏锐度和表达的强度的结合体,你现在陈述的只是一个方案,我不知道它们最终如何呈现?比如是不是在大的空间里面做一个复杂的装置?基于目前我对你的方案的了解,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把单张的放大出来,还能感受你要表达的东西,但像现在这样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我就感受不出来,好像它们在相互抵消,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你的作品呈现方式上有没有更细致的考虑?第二个是每一位艺术家都想对所处的时代有所描述和表达个人的理解,但是就我的理解,艺术家对时代的认识和感受应该体现为很强烈的情感刺激,不应该是过于理性化的理念说明,最后作品的呈现也应该是带有强烈的情感,你在进行了这么复杂的陈述之后,作品最后能不能够把情感体验很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述说?
薛峰:我是一个多变的人,昨天的方案在今天会有变化,其实总是处在犹豫之中。今天在这里讲述的这些方案,也许明天就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面的,在我认为没有结束之前,方案还在继续生长。“复杂”是我很喜欢的概念,在复杂当中去寻找新的可能性,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体现一种举重若轻,我在这里面找到线索,提炼出来,转换到自己的绘画语言系统中。自从在学校接受教育中所积累的认识和经验,在今天几乎是无效的,那么这种教育对我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也使我在新的是非新旧价值观中寻找一种判断。用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应对今天的需求了,就像艺术的今天也是这样。我把这部分认识当做理性情感。当然,现在的实验是在体现问题,在呈现方式上的考虑和情感的表达需要深入。
蓝庆伟: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绘画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搜集的文献、资料等一方面是绘画的起点,另一方面绘画又消解在这种原始资料里面。在他们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抽象的因素,这种抽象躲在具象的物象后面,附于绘画巨大的文化容量。在作品《亚洲地图》对地域的开放性思考之后,陈彧君、陈彧凡收回了视线,从自己生存的空间挖掘更多的可能性。他们从平面之内发现了空间的错位与关联,并尝试在平面内部塑造无限深入的空间。在他们这一系列中,二人再次对从平面到空间、从个人具体生活到人类文化环境的转换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下面有请陈彧君介绍他们二人最近的工作!
陈彧君:我想艺术家过多地阐述自己的作品,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观看作品之前。因为视觉的东西就是有它自己的表述方式,语言很难表达到位;一旦言过,极可能把视觉中所构架的逻辑关系简单化或一元化。所以还是先请大家看作品,之后再来交流。
郭燕:刚看了你的工作室照片,感觉特别想一个梦工厂,我看到你的作品中有很多东南亚的元素在里面,那么你是怎么想表现家谱的渊源?
陈彧君:其实很多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只是那时还没这么清晰,我们也是通过时间和实践来逐步明晰自己究竟要做什么。从个人角度看,中国当代艺术中与自己共鸣的东西不多,要真实来面对创作的话,我必须回到自己的生活资源中去寻找,于是就选择了家谱这一线索来做作品。另外,我们也想借这样一种向前追问的方式来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形成今天这个观念?我想,追述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做这项创作最大的诱惑和意义。
魏星:你谈到你的作品跟地理和历史时间的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家谱、族群文化生态,移居海外的历史等这些文献背景的线索。你的作品是和个人家族的经验、历史记忆有关系,那么你在一个美术馆、一个公共的空间展出作品,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都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当你去展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与观众的关系?因为当代的艺术作品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当观众参与,与他们产生互动关系的时候才得以完成,观众有可能会认为这是个体的经验,与他们无关,那么你是怎么处理你的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这种看与被看之间的联系的?它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去呈现?怎样把一种个人和个体的叙事与经验经由作品的转化介入到一般人群的集体意识中?
陈彧君:这个问题我把它理解为两个层面的话题,一个是关于艺术如何有效传递,另一个是衍生出的话题——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关于个人经验与他人解读的问题,其实之前也一直企图去解决,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我还是觉得把自己内部功课做好是最重要的,如果能把自己所思考的东西都呈现出来的话,那其它的东西对我而言可以说是额外之事了。此外,我也是希望观众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寻找到自己的逻辑关系或判断,这也是有趣的。而关于艺术的意义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经常会有学生问我:“老师,你为什么还在画画?难道就是为了赚钱吗?”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所谓的“艺术家”到底是什么一个概念?艺术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才可能搞清楚为什么自己还在做这个事情。在这场次贷危机面前可以看到,所谓的文化其实是很微弱的,可能对其他人而言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但我就是这么认为:艺术所能解决的还是个人的问题。我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当做自我精神治疗的一种方式。所谓新的绘画,我没看到,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悲观的情绪,我在现实中间找不到对应,也许是自我封闭造成的,但艺术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对自己阐释一个共识,这个共识跟你自己的经历和判断有关,其它的都是额外的事了!
杭春晓:我发现,你提出的问题是艺术到底有没有宏观价值?到底是个人性的,还是能够介入他人性的社会?如果,艺术没有一个宏观的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艺术?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瓦萨里说过:“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是后世艺术家永远无法超越的”,意思是说文艺复兴因其艺术的精确追求影响到当时欧洲的数理发展,并进而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我想,这一点足以证明艺术应该具有一种他性的宏观价值。我想问,如果你认为艺术没有这样的价值,那么你为什么要做艺术?你说到艺术是对个人的一种疗伤,那么你的一件悬挂作品,由“点”构成的佛像图案,是怎么用这件作品疗伤的?
陈彧君:其实我并不是在否认文化的意义,问题是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所提出的很多话题是伪话题,它的本质不是在解决任何文化问题而是经济效益的问题。那些悬挂的是陈彧凡的作品,我代他回答一下,他做这系列作品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呈现一个图像,而是想通过烧香的方式把纸本摧毁,这种摧毁的过程也是他那个阶段自我排解的有效手段。所以,最后所呈现的图像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痕迹所记录的某种过程。
郭赟:我想问杭春晓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谈的关于艺术的意义的问题,贡布里希说过:“艺术是一个不断释义的历史。”文艺复兴时的意识形态和当下的意识形态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当代艺术中的装置、影像这类,我们姑且称他们为艺术,那么又怎么界定它们的意义呢?
杭春晓:每个时期的艺术呈现方式都有各自的解读和阐释方式,我所引用的瓦萨里的话,不是指艺术史内部的问题的自我阐释,而是指艺术与人的社会相关联的一个东西——它竟然能够触发欧洲英国批量化生产的产业革命!这样一个角度,也就说在这个时期艺术,绝不是我们所想的艺术史自身内部的意义,而是一个社会学的意义,一个宏观性的意义。而后来的艺术,不管它使用了什么样的艺术方式,只不过是在艺术史内部释意的问题,到二十世纪以后,乃至今天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它出现了上述意义的产生可能,因为当代的艺术更倾向于因为一种精神的直接反思而带来的一个社会学上的宏观意义。从这点上看,当代艺术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和未来。
郝青松:杭州的艺术家在整体上还是与其他地方的艺术家有所不同,我感受到一种对知识的探求,但是难道我们做的只是对知识的反映吗?我们还应该强调知识的意图是什么,不只是反映,而应该是反应,就是强调知识的主动性。刚才陈彧君谈到对艺术非常地悲观,以及艺术的无效性,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是我认为,在社会进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无奈的宿命,而艺术是与我们的生命相通的事业,我们的职业就是艺术,它应该有一种主动性,不能纵容这种悲观的情绪而无所作为。
刘明亮: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个人的东西,每一个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放在文化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碎片,而这些碎片在历史的长河中必须整合,否则,其理解的意义就不大了,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恰恰是一条河流,是延续性的,每一个碎片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种普遍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体现。
蓝庆伟:我们看到了陈彧君对当代艺术的悲观,也看到了杭春晓老师对当代艺术的悲观。但是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史,我们可以通过追述往昔,来实现我们的夙愿,但是作为今天,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好的个体,个体还是要往前冲,具体关于其他文化、领域的知识,我想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形成的历史文脉的冲击。下面发言的是西安美术学院教师王风华,王老师用对城市的记录,来展现他心中的昨天与今天、往昔与未来、国内与国外的关于城市建设的思考。
王风华:今天有幸来到这里与大家进行交流和碰撞,关于新绘画的概念,我很难用几句话把它概括出来,倒是自己有些学习经历和创作体会可以谈一谈。2000年以后,我陆续参加了一些国外的艺术家交流项目或展览,尤其在英国和德国的学习,拓展了我对绘画艺术的认知。至于什么是新绘画的命题,我想其实并不重要,当我看到Chris Ofili、Gary Hume、Neo Rauch、Daniel Richter、Peter Doig等这些人的作品时,我会想这些可能就是新绘画吧。因为他们改变了我对绘画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颠覆了我对传统绘画的创作方法和观念。我为什么选择城市作为创作主题,是因为我曾经迷失在西方的艺术世界里,参观国外的艺术家工作室时,我非常困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的绘画?我要表达什么?说实话,在西方我真的没有想清楚,可是当从一个欧洲城市突然回到北京,这种东西方城市之间的反差,不论从视觉到心理都极为不同,那一刻我看到的中国城市大概才是最真实的,后来我开始留意曾经被我们漠视的生存环境。拍了大量的照片进行分析,我很难找出中国城市之间的独有个性,尤其二级城市更是很难区分,比如太原、石家庄、郑州或是西安等,除了标志性建筑之外,所有的小区、楼盘、街道都几乎相同地把上海和深圳作为发展的模式,这也暴露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我们拆掉了非常多的旧房子,盖起了一幢幢相同的大楼。还有瓷砖这种廉价的建材充斥着所有大街小巷,也许是我最熟悉的和最能表达的。此后的几年间我一直在创作《城市系列》绘画作品,希望通过绘画和其他方式传达我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态度。今天我展示的作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绘画,另外还有一个影像作品《立杆见影》,影像主题选择了城市中的电线杆这一中国城市特有标志,也是城市和人的关系,这部片子拍的都是中国城市的细节,为什么叫《立杆见影》呢?画面中是有杆有影,延伸到成语“立竿见影”,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要立竿见影地步入现代化,还来不及把电线埋到地下,大家对电线杆都已经漠视地遗忘了,可是它实实在在的立在每个街头,从798门口就能看到头顶缠绕的电线和数不清的电杆。
下面我就西安的城市建设来分析一下中国城市的规划方向:这张照片是西安的大雁塔,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唐代建筑遗存,但是几年前在它旁边修建了亚洲最大的喷泉广场,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每天晚上霓虹射灯和喷泉会吸引无数观众,看起来很炫,但破坏了建筑和寺院本来的古朴;这张是大唐芙蓉园,政府花了13亿人民币复原了唐代的皇家园林,占地一千亩,广告词是“国人震撼,世界惊奇”;这张照片是西安市政府投资140亿修建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号称是世界最大的主题公园;这张仿古一条街,是把老房子老街道拆掉,重修了很多仿古的建筑,又把高层公寓统一规划成假古董,我想把这些关注的问题通过艺术呈现出来。
现在大家看的是我几个阶段的绘画作品,这张《延安的1949》,主要表达新中国成立时红色首都被历史封尘的图景;这张《1979年南京的某区》,工厂、学校、住宅混杂在一起,这也是特殊历史阶段的城市特质;这张《1982年福州》,主要表现中国第一批改革开放城市刚刚苏醒,还保留着很多文革的气息;这张《1997年沈阳》,让我们看到中国北方城市非常普遍的会展中心和广场……。后来我的视点从城市的大场景和鸟瞰,进入到了城市的局部,转移到了自己周围最熟悉的住宅小区。从这张《昨夜有雨》中我们能看到大量雷同的路灯、相似的报栏以及杂乱停放的私家车。2007年以后我开始创作《立杆见影》系列,也是具体到了城市零件的表现,这系列作品中都出现了水泥电线杆和玻璃幕墙,目的是想强化城市中的视觉垃圾和光污染。
李旭辉:您采用的照相写实手法,您把照片挪用到绘画,您想诠释一种中国城市的状态,艺术家面临这么多的图像,是怎么选择的?
王风华:我曾在照相写实的概念中来回纠缠,后来我就开始回避这种提法,宁愿称之为冷具象绘画。作品的传达跟照片有非常大的区别,创作过程是经历多次反复的,也实验了多种手法来表现,其实在制作图片时为了强化画面的视觉感受,我加强了构成因素,采取多幅原始素材的拼接,而非单纯的还原照片。如果了解我的创作状态的话,就会明白我选择图像是为了如何去强化主体,如何能更好地说明我想提出的问题,如何表达我对城市建设的态度,这是我对图像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创作环节。
刘明亮:今天一直在讨论新绘画的问题,从你的绘画出发,你是怎么实践这种新绘画的理念的?
王风华:我理解的新绘画是相对与过去已经约定熟成的模式化的东西有所突破,新绘画不仅是个图式的问题,还有视觉、观念、材料、技巧、心理暗示或生理反应等等,传递出一种当代气息,比如我们从John Currin的作品中能看到丢勒的语言,但是传达出来的气息却是当代观念,这是我对新绘画的理解。在我的创作实践中也吸收了照相写实主义和超平面艺术,以及抽象绘画的语言和方法。所以我认为具有建设性的实验和视觉贡献,或是具有强烈时代气质的作品,都具有新绘画的特质。
蓝庆伟:谢谢王风华老师,下面我们有请陈辉。
陈辉:
大家好,我主要介绍我两件摄影作品,一件是2007年的,另外一件是2006年。2007年作品的叫《33224》,是一组数字,拍摄地点在南京的明代建筑灵谷寺。它在民国时期设置为阵亡将士的纪念堂。所以它的墙壁上都刻满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死难将士的名字,一共是33224人,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物,现在它的功能在逐步丧失,变成一个招揽旅游生意的场所。在最初的设计意图上面,门窗都开的话,所有的名字应该是能看见的,光照都是比较充足的,但是现在为了简化管理和方便游人流通,前后只各开了一个门,窗一般都不开,所以刚走进去大门的时候,接近门的地方是能看见名字的,到里面黑暗情况下字是看不见的,就变得越往里面越暗,有的地方是加了白炽灯,白炽灯有一个照明的现象,受光的地方名字是能看到的,离光越远的地方名字是渐渐暗下去的。这件作品从第一次拍到最后完成经历的时间蛮长的,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对它的观察和描述,不是非常准确,自己感情的进入我觉得显得粗糙一点,这个地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参观过了,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再看才感受到它的价值,所以一直准备把这个作品好好做做,但是一开始用了各种手法,闪灯或者打各种光,但是总觉得不理想,后来干脆就是尊重它现实的光线,感受它在现实当中的存在。为什么选择手卷这种呈现方式呢,是因为随着观众展开和收拢,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也可以提供一种细致而具体的触摸感,这是传统绘画经常选择的方式。手卷这种形式呢,我觉得是能够表达我心理状况和感受,就是从亮处开始慢慢随着观看地延展,渐渐向黑暗当中过渡,过渡到视觉的全黑状态。或者从全黑的地方开始,然后渐渐向光亮的地方过渡,渐渐过渡到名字全部呈现的状态。这在屏幕上大致可以演示一下看这件作品的感受。比如说这是手卷开始展开的时候,是视觉正常的部分,然后随着手卷慢慢展开,就会有光线渐渐变暗的过程。到最后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它是图像和人消逝的过程。我一共拍了八条,因为许多碑和名单都处在黑暗当中根本拍不起来,如果可以全部拍下来,就都是一条条黑暗的长卷。我拍摄的时候碑上具体的名字常常会忽略,当在电脑中制作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和一些熟人相同的名字在上面,有一次我还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刻在上面。《33224》是我2007年完成的作品。
另外一件作品《是谁》。2004年,我在为旅游观光而设的纪念馆中见到了一组蜡像,他们是中国努力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代表人物,由于制作的随意粗劣和保管陈列的漫不经心,蜡像低劣、污损和残破,蜡像的领带和西服什么都是很低劣的那种,就是很便宜的那种产品,主要就是借一个纪念馆的名义收点门票之类的。最早我被蜡像荒诞的表情、动作和人物关系吸引,拍了些猎奇照片,接下来的两年,去了多次以后,就把它当自拍像来拍,一切只剩下架稳相机慢慢曝光了,作品的名字叫《是谁》但是还是可以把它的名字讲一下,这件是在日本投海的陈天华,背后还有富士山和樱花。这件是鲍罗廷,好像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中国有事外国人也很忙。这个屡次失败的人叫黄兴。蔡元培,很像我熟识的一位半生辛劳的长者。几张照片都是当作自拍像,尤其宋教仁这幅感受最深。
蓝庆伟:下面请大家提问。
邱忠鸣:您好。您的这个作品,离不开那个手卷。其实那个里面我觉得信息量非常大,我个人的感受也非常地丰富。比如说像您这件作品里碑上刻的原本是辛亥革命阵亡将士的名单,是吗?
陈辉:阵亡将士的名单来自北伐和抗战期间的淞沪会战,而且主要由几个地域组成,比如说安徽,浙江等这几个省。
邱忠鸣:与战争的关系,就是把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也是一个纪念碑性质的东西。其实事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以前的纪念碑,今天的旅游景点,而你作为艺术家用摄影装置的手法去处理这样一段历史记忆。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历史记忆与当下境遇、“革命先驱”与日常生活、民族国家与生存状态、阵亡将士与艺术家……交错纠结。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你说好像在这个名单里面你还看到了熟人,甚至包括你自己的名字,这个也很有意思。让我想到一些终极问题:人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以前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我个人感受到有一种轮回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感受语言很难描述。包括你用自然光来拍摄这样一件作品,一开始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然后中间看不太清楚,然后再到后面什么都看不见,直到最后又回到清楚。这种用光的手法也提示我好像有一种轮回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你选择手卷这种形式。我对你这个展示的方式比较感兴趣。正像你一开始说的,你觉得手卷在观看的时候是展开看一段,然后再卷一段,然后再展开、再卷,不断展开与卷起的这样一个过程。手卷观看的过程当然像你说的伴随着一个时间流动的问题。这个过程和西方艺术的表达手段很不一样,观看方式也不一样,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两种看世界的方式。除了提示时间的流动外,手卷还应该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手卷,在以前文人们观看的时候,很多情况都是三五知己雅集在文人的书斋里,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用刚才这样一种不断展开不断卷起的方式,然后观看的距离可能就是一个手臂的距离。其展示的空间也是一个封闭性的私密空间。这里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用手卷这种方式在这个作品展示的时候,展示方式上有一个转换,将以前文人雅集的私密空间转换成一个和许多观众交流的公共空间。你当时展示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你是怎样处理作品和作品展示的方式与空间的关系的?因为最终一件作品是要和观众对话的。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陈辉:首先直接回答一下问题,展示的时候,观众是可以随意翻阅的,据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部分观众很熟悉手卷的阅读,一部分观众开始有点生疏,慢慢也能摸索出一种观看的方式。然后我再想讲为什么选择手卷这种方式,手卷说老实话是一种太有雅玩性质的东西,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但是它能提供的那种时间地流动和情绪变化的功能,我关注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人名和他们的来源,我刚才讲的是具体的战争啊什么的,其实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被组织在大的叙事当中,只是赋予了单一的军中职务,其余的都是被忽视的。当我制作的图片的时候几乎每个名字都会看到,每个人都被重新感受到,名字还原为人,还原为所有的人,我就会发现他们是不是逝去在某次战争显得不是非常重要了。
杭春晓: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你拍那个蜡像的时候,是当做一个自画像来拍,那么,具体怎么展开的呢?还有,你也画画,你做摄影和画画有没有一种关联?
陈辉: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把《是谁》当作自拍像,一开始我在几年前第一次拍这组作品的时候,完全把它当作一个被取笑的粗糙蜡像,完全被它一些新奇的、低劣的、滑稽荒诞的东西所吸引,就是后来去的多了,慢慢地相互之间有了一种沟通,慢慢地觉得这种污垢残破,粗糙低劣都是自己经受过的,感受过的,也就能够体会到他们内心的那种东西。对于我来讲,拍到最后它们已经变成鲜活的人物,甚至是有一种镜像的关系。虽然五官可能是不一样。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摄影和绘画的关系,我一直想寻求一种现实和历史内在的张力。但这种张力我很难表述,绘画中一直没找让自己很爽的者一种表达。现在我转移一下阵地,挪到照片这块来,来表达一下,说老实话关于画画,我失败的作品比较多。
郝青松:对于第一件作品我很感兴趣。让我想到最近媒体上不断披露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人在缅甸征战真相的事情,也包括有相关剧情的电视剧,这一切的目的似乎都是在恢复历史的真相,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队做出的真正的努力。我还想到张大力最近的作品,他把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发现的一些老照片,和我们在公共场合看到的这些照片做了一个对比,揭示出这些照片是怎样被篡改的,他的意图就是直指掩盖真相者的目的。这样的作品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也很有力度。我感觉你的第一件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力量。我的疑问是,你第一件作品里面的光源的处理,有一幅是光源从侧面开始慢慢的减弱,这样的形式和作品中意图的吻合非常好,但是另外一幅画面中出现在中间的光源,据你的解释是因为一种偶然性,而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削弱作品意义的可能性,不能达到上一幅中形式和意图的吻合程度。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创作方法只是一种惯性的沿用时,是值得怀疑的。我想到上午发言的艺术家孙芙蓉的作品,她用剪刀剪中山装,那是她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服装,是时代的符号,我们都会理解,但是当把这种方式继续用在西装和迷彩服上,就是当这种创作方法盲目地惯性延用时,事实上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一种转移,或者说已经有一种模糊性。那么你的第二件作品,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模糊性。作品的名字《是谁》,但是你针对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些蜡像本身是一种在技术上不太成熟的可以说拙劣的模仿,那么你又像第一件作品那样来模仿它,这就真的是个问题了,你最后的意图就会很模糊。
陈辉:第一个问题我理解的不是太清晰,我就以我不太清晰的理解来回答。你举例的光线偶然性的问题,它确实存在的。它的初衷确实是想把名单全部照出来,只是敷衍了,随便放的,才形成了这种明暗效应。真实就是在没有光的当中,在消失中,而不是在被照出的部分,被我们看到和识别的当中,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蜡像做的非常精细我把它拍下来就变成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它的拙劣和粗糙,荒诞和滑稽,反而更像我的写照。我认为,如果它做的非常精美,那我也就不可能来拍了。
蓝庆伟:谢谢陈辉老师,下面我们有请包忠老师。包忠老师那个是根据自己的创作来谈他所理解的新绘画以及新艺术的边界问题。
包忠:对于新绘画及其边界的问题其实之前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知道绘画或者说艺术要寻求突破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而“突破”就需要探索那个“边界”在哪里。传统绘画的确有深远的历史和无穷的魅力,而对于他们发生的当时来讲它们都是当代的,对于传统的延承我更愿意从精神的和世界观的层面去学习而不仅仅是技法和图式,而在当代,绘画早已不是表达精神的唯一方式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落后了,相反它更自由了。绘画对于我来讲从一开始去寻求一些在语言上的突破就选择了这种黑颜色的底色,当时觉得黑色是一个极致的颜色,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个颜色。画面里面的图像大都放置在画面的中间,从这个形式上来讲,就是有点特别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绘画形式,而只是在造物,在一个极致的幽静而理性的空间里造物,希望这些物象本身或者物象之间所形成的修辞能够对应出某种心理现实,我说的这个心理现实大概指的是现实表象之下在人的心理层面所沉淀下来的某种东西。这张是比较早的一张作品,画的是一个记事本的载体,我想记事本就是一个承载时空的东西,可以承载很多东西,关于时间和记忆的,在看上去冷漠的画面背后其实也许是某种巨大的情感。这个是封存系列,画的是密封袋,密封袋其实也是一件容器,也是希望留住一些记忆的痕迹。这后面有一些感叹的东西,因为意识到存在的不可靠,存在就意味着即将消逝,存在都只是些飘渺的瞬间。
这个画面上的形象我不太刻意一定要去画确定的人物或者动物,只是特别强调它是某种有确定意义的东西,一个形象就好,我想这样对于表达来讲可以更自由一些。这个看的不太清楚,因为下面有一个很细的圆形轨道,我想用它象征某种人的心灵的轮回,这样两个形象在这个轨道上相遇,这件作品的名字就叫相遇,而相遇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要说到跨学科领域对绘画作品的影响,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画的是某种动物或者莫名生物的骨头。这些图像的来源是一些生物学或者考古学研究意义上的图像,我想我制作这种画面的过程有点像模仿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做研究的那种工作姿态。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有点类似于科学家去探索世界,去阐释世界的工作,只是认知的角度不太一样。这个是科学对我的影响,画的是一个很小的翅膀,希望自己像一个科学家那样去研究事物剖析真相。在图像上面我也不太愿意把自己固定在纯黑底色。比如说这些画的就是纪念碑系列的东西。但不只是纪念碑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不是纯黑的底色对于我来讲带有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在里面。纯黑色是比较纯净而冷静,比较极端的,有些色彩和空间在里面可能会造成相对比较温和的画面感觉。但是它还是一个容器,就是纪念碑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容器,相对于纯黑底色的作品来说,作品内在所关注的东西是一致的。图像和图像之间有一些并置所产生的对应或者矛盾的东西,就像两个词语的并置也会让一个句子含有某种意义。
这张画的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圈套,这个图像的想法来自于一张夜晚的立交桥的照片,立交桥上有川流不息的汽车。但是我把它重新演绎了一下,让它看上去四通八达,但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圈套,没有起点和终点,循环往复。这种感觉有点荒诞,有点像卡夫卡的《城堡》给我的感觉。同时在图像上也受了埃舍尔的版画的影响。我觉得他的画特别有意思。水明明是从高处一直往下流,却很自然的回到了起点。还有那张在城堡上排成一排的僧侣一直往上走,看着是一直往上走,却又走回到了起点,这个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埃舍尔的作品肯定不只是一个视觉错误的作品,它应该有一定的哲学上的涵义。
这个是我比较早的时侯做过的一个图片作品,拍的是一个化学用的量筒,装了一半的水,这两张图片实际上拍的是同一个量筒。然而却得出来两个不同的结论,一半是空的,一半是满的。这个作品我想讨论的是人们对待相同事物的是非观的问题,根据不同的角度对相同事物加以判断,如果一定要有结论的话,可能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矛盾的。这件作品其实我自己也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它,你可以说它有一半水,但是如果一定要对它到底一半是空的还是满的进行判断,好像真的是得不到结论。我想这个作品是因为很久以前看了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罗生门》也是这样一个关于真相判断的命题,同样一个偶发的事件在每一个供述者的口中都因为个人的利益和情感而变得不同。人证显得那么的不可靠,而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答案永远的被淹没了。《罗生门》问题在我们身边是无处不在的,这样的感受让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这些图片作品在内容上其实也呼应了我绘画作品背后的一些思考。
蓝庆伟:好,下面请大家提问。谢谢包忠。
黄一山:包老师你好,之前就听说过你的作品,但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刚才带来的作品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我对你那件心灵的作品感觉比较有兴趣,因为你在这里面提出一个跨学科的态度和工作手法,然后跨学科应该更确切说的是模仿另外一个学科的口吻来做艺术。但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在模仿的生物学家的做标本的时候,这两件作品你没有做任何的改装,这使得我没有办法从你的这两件作品看出你在说的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我就想请你说一下关于你那个模仿学科口吻的那两件作品中你是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包忠:我想模仿这个用词也许我用的不是太恰当,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在模仿,其实是想跨越所谓艺术家既有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我想我们既可以向纵向的美术史学习,也可以在横向的学科里得到启迪。谈到跨学科,还是应该着眼于突破所谓艺术的既定概念,语境开放了,姿态也应该开放。我们不一定只是站在所谓艺术的角度去思考和工作,科学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域,因为科学家在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去解说这个世界探索未知世界,需要绝对的理性和逻辑,而艺术家的工作其实也是在精神层面上去阐释世界表达情感,这个情感也可以通过冷静而理性地剖析来表达。
蓝庆伟:张小涛为大家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代替陈卫闽老师讲解他的创作;另一部分是讲他自己的新作。
张小涛:今天介绍一位我的老师陈卫闽,我有必要纠正一个概念,大家都觉得四川绘画很商业、很符号化,其实在四川有很多实验的艺术家,比如陈卫闽、朱小禾、陈秋林、李华生、李一凡等。在四川艺术家群体中,陈卫闽是一位远离于潮流之外的艺术家,从艺多年坚持自己的精神诉求和语言实验,他以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和整理转换成独特的绘画语言,以图像写作来建立自己的视觉“档案馆”,他在今天的新绘画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意义。陈卫闽也是被商业或者是主流学术所屏蔽的一位艺术家,我写了这篇《县城经验——陈卫闽的城乡结合部“档案馆”》文章在网上有,写文章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又有写作的冲动,因为这种被屏蔽的历史是不会被市场、体制和批评家系统所关注的。2000年,陈卫闽选择了作为修辞的叙事,进入了“微观叙事”,远离了符号化倾向的“宏大叙事”,用社会学图像的“显微镜”去剖析社会的细胞,通过档案的收集和整理,与先前的表现主义美学拉开距离。他早年是学舞台美术的,在四川南充市歌舞团里当美工,其实他2000年之后的绘画有点回到舞台美术,早期在南充生活的经历也许有莫兰迪类似的体验和心境,他果断把反思历史的“宏大叙事”方法摒弃了,运用了全新的“微观叙事”修辞,从符号化的绘画转向不确定的图像方法,作品具有不可预知性,这与2000年以来新绘画的实践中的图像方法类似,从网络、大众流行文化、艺术史的图像中找到了新的资源,画面是关于乡土广告、符号、标语,凡是在乡村里看到的所有信息在他绘画里都有呈现,当时还没有谈社会学转向,2004-2005年批评家在谈社会学转向的时候,更多谈的是政治化、符号化的东西。档案也是艺术,这是视觉档案,我想这种积累并建立起谱系是非常有价值的。陈卫闽的绘画语言中有一种乡村的波普,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他在绘画语言上是有建树的,并不是随便的来呈现一个东西,关键是观念、课题找到了,艺术语言就会在艺术史上留给大家一个讨论和深入研究的空间。后来,他的画面更像是一个舞台,画面建筑上的广告、标语成为一种背景,天空成为舞台的背景,有一种舞台化的倾向,他后来把舞台后面的墙作为一个载体,他在这种图饰里面尽可能的找到语言的变化,当你找到一种课题时,就应该不断通过语言的挖掘,使得绘画最后还是回到直觉上来,而不是说教。这其实是考证之后,通过视觉的感染力转换出打动人的图像。
也许今天的黄桷坪被陈卫闽的绘画不幸言中,满街的涂鸦更加强化了这种郊区的特征,铺天盖地的广告涂鸦比陈卫闽的绘画还要让人恐惧和头晕目眩,今天的黄桷坪是一个巨大的县城,美院的高雅学术殿堂、电厂的工业化痕迹、黄桷坪的市井生活、望江、交通茶馆的信息流通等构成了这里丰富而充满生机的“乡镇生活”,脏乱差的街道和彪悍的民风,与今日的满街涂鸦真正的“和谐”了。陈卫闽最近带学生去贵阳写生,精神病发作,现在还住在贵阳的精神病医院,他对艺术的虔诚有点像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