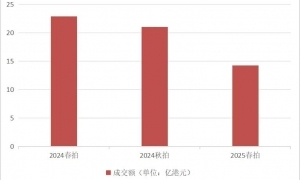Wim Delvoye
记者:很高兴在中国见到您,Wim Delvoye 先生。
Wim:你好!
记者: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吗?
Wim:不是的,我已经来了中国很多次了, 我在北京周边有一个农场, 有时我会每个月来一次。但这次在新北京的展览是我第一个在中国的个展。
记者:您之前好像在 “798”参加了一个群展?
Wim:是的,那是冯博一策划的,是一次很好的经历。但那次只展出了一头猪。这次有四头,并且它们的纹身也很有中国的味道。
记者:能简短的介绍一下您这次带来的作品吗?
Wim:好的。首先是Cloaca 这个大机器,这是Cloaca第四代,他每天都要吃,要消化,要拉。我们每天喂它3次,他有正常的摄入量以及每天4-5 千克的排出量,这次开始时,我们要喂它吃中国食品。
还有4头纹身猪,它们身上的纹身都是中国图案,并于Cloaca一同展出。
这次我还带来了淡蓝色的像装芭比娃娃一样的盒子,但里面不是芭比,而是我和我的机器。
记者:Cloaca 非常复杂,您是如何使它达到今天这个程度的呢?
Wim: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做一个大的机器。从90年代早期开始,我就开始构思,构思是否有可能做成这件作品。2000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完成了第一台Cloaca, 过了一年,我们又完成了第二台,然后2003年第三台。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七台机器了,五台被测试过,两台没有。
记者:我们知道,这台机器的制成,知识面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还有很多工业,化学等方面的科技。那您前期是怎样构思,怎样准备的呢?
Wim:这需要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要经历很多过程。我们想复制的不是形式,而是功能。就像我们的大脑一样,电脑能模仿大脑的功能,为什么我们不做个大胃来模仿胃的功能?我们要考虑很多方面,考虑环境,酸性,温度等。在排泄方面,我们想就像机器产出啤酒,产出奶酪一样,它们都是排出产品。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吃了多少已经是排出的东西。所以我以人们制作食品的方式制作粪便。
记者:我们听到策展人介绍说,当Cloaca 入海关时,人们不认为它是一件艺术品, 最后而把它归为了教学用品一类。在您看来,艺术品在本身的科技含量和它本身的性质——“艺术”双方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Wim:我认为它是艺术,因为它完全没有用处。也许有一天有个科学家说“啊,我可以用这个机器”,当这个机器真的很有用,非常有用的时候,也许会超过艺术本身。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它不是用来得诺贝尔奖的,它仅仅是个排泄的机器。并且这部机器不能用自己的能量存活,需要人的照料,它是毫无用处的,是一件真正艺术品。
记者:您之前指出过您已经有七台机器了,第一台是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局限性及可能性;第二台是更加贴进工业化标准的,第三台则是为了扩大生产率。那么第四台是怎样的呢?
Wim:与第三台的效果一样,我们希望第四台也提高产量。但是这台比之前的小很多。以前的都是从左到右的程序,但这台是从上到下,并且提及更小,更像一件雕塑。其实这几台机器的改良就像公司制作产品一样,我们和制造商有着相同的逻辑。比如你是一家摩托车公司,当你成功后就会想要制造汽车,之后又想制作卡车……你总是想要提高产率。我们也是一样,时间是一定的,所以只能提高效率。但这些机器每台都有它们的优势。
记者:我们知道您参加过很多国际展览,如卡塞尔文献展等。Cloaca也一定在国际大展中展出过。与国外的观众相比,你觉得中国的观众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Wim:其实前两天就有中国人已经见过这个机器了。我认为人们的反应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机器,也都有大便,中国也是一样。无论人们的语言也好,文化也好,Cloaca 对他们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每个人都与Cloaca有联系,每个人都可以跟Cloaca对话。
记者:我想问一下这个作品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它是这件艺术品物质性的一部分吗?
Wim:我认为艺术应当是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很简单的细节,比如说厕所,吃饭等等,非常简单。我的作品就是模仿了一个简单的消化过程,它要请客每一个人参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
记者:我们了解到这次这四头猪会和机器一起展出,这是第一次吗?你怎么看待它?
Wim:是的。我感到很兴奋!这次你可以等着瞧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也会得到很多好的图片。这些猪,你不能控制它们,它们可能在左,也可能在右。这个机器也是一样,也许很通畅,也许会“便秘”,也许是浅黄色,也许是深黄色……我们都不知道,就像照顾两个小孩一样,所有的人都要给它们食物,要为它们打扫,就像一个话剧一样。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个在顺义的艺术农场,您怎么定义它呢?
Wim:我们三年前新建了一个在顺义农场,当时只有几头猪。今年是猪年,我希望数量会有所增加。我们在猪很小的时候就在它背上纹上小图案的纹身,图案会随着猪的长大而变大。其实是自然的作用,而我们是受益者。
记者:也就是说在猪还很小的时候,你们就在它的身上刺上纹身。那么为什么选择猪呢?
Wim:因为猪长得很快,这是一个原因。再有就是猪很能代表资本主义。人们在农场养猪,就像是在银行里存钱,为了保证肉的新鲜,你不会杀掉猪,而是让肉长在上面,当需要时再杀着吃。就像存钱罐一样,外表是猪的形状,把钱放在里面。
记者:所以说养猪也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
Wim:是的。
记者:不知您是否看过中国艺术家徐冰的作品,他也用了猪作为其作品的元素。您是怎样看待他对猪的使用的呢?
Wim:是的,我听说过。很多的朋友都发明信片告诉过我。我想中国的艺术家对猪着迷是很符合逻辑的。首先,猪是很中国化的一种动物;其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里有很多种工业,但农业仍然是站最主要的位置的;再有,猪在中国代表着很多好的事情,比如幸运,钱财,健康,有很多孩子等等。所以很多的艺术家都对猪着迷。
记者:现在,影像装置非常流行。我们知道,影响注重的是时间,装置注重的是空间。那么在艺术家的创作期间,时间和空间之间是怎样协调的呢?
Wim:我们用影像来做纪录片,现在也有很多的艺术家用影像和装置结合起来来做作品,但用影像是为了它投射在墙上时那种特殊的表现。我认为大多数的艺术家都能够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影像有时也有表演的元素在里面。但就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装置艺术家。
【编辑:虹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