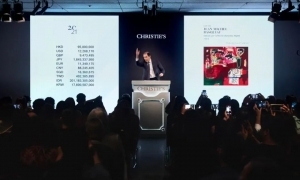真实的象征与想象
赵力
曾红梅《新东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剧烈的变化。而在这一剧烈变化之中,人们或者茫然无措,或者浮躁痴迷,以至于深陷那些自我刻意营造的“奇景幻象”,却对于真实生活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于是真实的世界似乎随着变化的加剧,从我们的视野中渐渐失落,开始隐蔽而又缄默地蛰伏起来。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艺术创作关于当下生活的表述也成为了所谓的“格式化”理解,“都市生活”苍白地只剩下了俊男美女、咖啡馆、健身房、汽车、大厦……,“乡村生活”不是被“猎奇观赏”,就是被“考古发现”,作品大多充塞着“精英们”的无聊调侃、“富足者”的多愁伤感,以及“新新人类们”的恣肆放纵。事实上不断前行的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必须改变的就是这种轻视慢待真实社会生活的积习,因为正视社会、反映现实,就是正视当代社会中的生命真实,就是关注人类的自身现状与生存发展。
作为年轻一代的雕塑艺术家,曾红梅要走的艺术之路不是“一条众人脚下的老路”。90年代曾红梅的创作,既体现出年轻人对于新兴艺术潮流的好奇与模仿,又反映出不自觉地尝试与实践。虽然风格没有定型,题材并不专一,但是很多作品构思大胆且手法多样。这一时期曾红梅的雕塑创作大致上形成了两个特点,一为有意识地拼接,一为夸张性的变形。所谓“有意识地拼接”,主要是指艺术家往往将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结合起来的方式,譬如“人体”与“物体”的拼接,“人体”与“人体”的拼接,以及“物体”与“物体”的拼接,这造成了视觉上的某种惊诧以及由此而生的冲击力;所谓的“夸张性的变形”,则是艺术家在具体造型和形体表现上更侧重于漫画性与夸张性的手法,从而促使自己的艺术语言向反讽性、象征性与寓言性的转变。即便采用了“有意识地拼接”和“夸张性地变形”,但是曾红梅的创作初衷仍在于针对现实生活的真相探寻,针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不仅大量的素材直接来自当下生活的本身,同时作品所表述的意涵也直刺当下生活中极度敏感的部分。
作为女性的年轻艺术家,曾红梅也在近期的创作中开始张扬自己的“女性观”。她的“北京人系列”,或许令人联想到哥伦比亚艺术家博特罗的创作——那种膨胀而夸张的“胖女人”形象,但是与博特罗的“男性立场”和女性作为“被表述的对象”所不同的是,曾红梅或许试图借用这一形象,用以颠覆当下生活中的习惯偏见。正如博特罗“运用这种膨胀的人物形象来批评哥伦比亚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理念”那样,曾红梅的“胖女人”也以一种夸张的手法,既泛然批判当下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同时更从女性的立场,以迥异于“当下瘦身文化”的“胖女”形象,针对在父权体制下社会象征意义的转化,揭示关乎女性的“可理解的身体”与“有用的身体”等概念的生成过程,反映女性在“当下的扭曲的社会生活中”的“主动顺从”甚至是“失去了自我”的现实,遂形成了某种的“自我反省”。
在近期创作的另一系列“市井百态”中,曾红梅同样表达出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其它看法。与其他艺术家所不同的是,年轻艺术家也有意识地去扭转“社会底层往往被漠视或者总是被描述的那些现状”。曾红梅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不是为了展示人生的苦痛,或者一些社会的阴暗面,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身份优越感,而是为着正视当代社会中生命的真实,以及真切反映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保安”、“晨练”、“看车人”、“值班”无疑是当下生活中那些“小人物”中的代表,曾红梅不仅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甚至以同样夸张的手法,传达出“那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惬意——生活在底层,享受的是阳光、空气和清风,抛弃的是自私、腐化与浮夸。”
相关链接:
【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