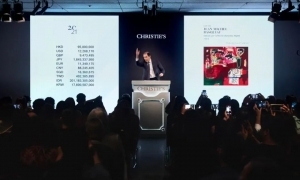继长安画派赵望云先生之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山水,试图通过改良审视与扬弃传统而直接进入现代解构状态绘画的后长安画派画家范炳南先生,近几十年来一直徘徊在所谓的“中国画坛,甚至是长安画坛”之外。在他看来,长安画派作为历史阶段诞生的一个画派,已经为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美术开拓与发展完成了使命,从而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划上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句号。那么长安画派之后,新的美术发展应该有谁来承担和传扬,这成为范炳南近半个世纪来一直苦苦探索实践的艺术追求和历史使命。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术体系经过明清两朝文人画家的反复演练,已经蜕变为空洞的程式化躯壳,情感的内蕴早已被抽空,与自然物象的关系也早已被切断,令人厌倦的千人一面的画法早已困扰着中国的画家,本世纪以来的大师们的小修小补小改小造并未损传统的完整性毫毛。以山水画的皴法为例,近代以来的所谓改造,不过是各种名目的传统皴法各自稍加变形而已。”
早在上世纪初,出生于四川的陈子庄先生就是在看到这种绘画现状的历史痼疾沉疴时,开始对传统产生怀疑,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他自觉意识到应对传统提出质疑,甚至还清醒的发现,不必过于依赖传统技法也能创作出完全的中国风格的绘画。如果欲求中国画继续走出新的自我,就必须解散过去那些陈腐而约定的世俗理论。把传统的解散看作一次“开天辟地”的新生,无疑会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一次可能性的“凤凰涅槃”。
“因为一个整体的、囫囵的传统对于现代人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被分解之后的传统才存在选择的可能、改造的可能。只有在这些出现以后,本来已成为现代中国绘画的负担的漫长而庞杂的旧传统,才会转化为滋养现代中国画创作的营养。”(引自并参考陈滞冬《陈子庄的意义》一文)
范炳南自师从赵望云和何海霞两位大师后,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历史使命和延伸长安画派艺术的抱负。为了在山水画上有所突破、创新,早在1989年,范炳南就选择去了美国。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心迹:“我去美国并不是为了“淘金”,而是遵循和实践何海霞先生交给自己的艺术使命。“彼时,他亦怀抱着“我要在山水画上有突破、创新,就要云游、改变自己的思绪。我选择了美国,去彻底改变自己的理念,重新审定中国画的章法、构图、设色、用笔”的理想与抱负。这个阶段,正是范炳南先生敢于冲破禁锢,以“立足长安,融汇东西”的大世界文化关照姿态,奔赴大洋彼岸从事“载酒时作凌云游”的探索发现和艺术实践。
先生自赴美国定居以后,在不间断从事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社会活动实践和沟架过程中,开始反刍思考中国传统水墨画在世界大文化背景和地球村意识形态下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现状。新时期以来,随着东西文化互相杂交融合,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元素时代合作中,换位思考并审定中国画的时代立场、美学思想和哲学意味,不断从隶属的东方文化情结里走出“小我的中国绘画”,站在世界多元素绘画语言里探求出路;甚至站在相反的立场和文化意识里积极总结和批判中国水墨具体应该怎样接受改造,保留和扬弃那些元素和历史成因上的审美盲区,使新时代下的中国画的探索与发现变得真实可信,甚至具备成功的可能;成为范炳南绘画艺术不断求新和寻求变法的重要所在。
在他看来:“解构传统,不是推倒传统。而是要具有传统,从传统那里找到普及与影响中国画家近一百年来何以萎靡不振甚或空洞虚弱,缺乏时代激情与情感火焰的艺术干扰因素深植在哪个环节里出现了问题!如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水墨画还将在传统与创新的两道胡同里并行而无法贯通。”
这种深刻而有悖传统改造法则的艺术思考令范炳南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游走不止。在他的个人艺术思想世界里,切断连接母体文化脐带的绘画艺术还能够活下去并能否继续强大且富有生命活力等问题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困扰;如何使传统在当代更富有魅力,在既不失母体传承又无限度激活绘画语言使其在当下的绘画世界里更富有现代意味和世界文化主流影响元素。
这一系列的重大绘画艺术思考与理论反刍,后来最终成为他绘画作品一直探索和追求的艺术主题。
艺术的思考与反刍是痛苦的,艺术的探索与实践又更是对画家的极端考验和漫长磨砺。在求得大世界文化艺术意识观分解之后的范炳南,终于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和特定审美价值取向中腾出足够的距离来理解长安画派作为中国画分支中的一朵奇葩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性突破;而这种开创性的突破势必会引发新的美术理念与创作手段的变异、变法,这个变异、变法决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从中国
【编辑:芳若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