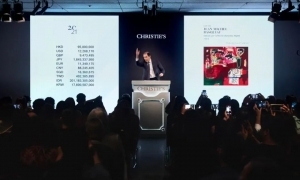时间:2010年11月29日
地点:文达画廊
张光华: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我最钦佩陈老师的是您在28岁便获得副教授技术资格、32岁就获得教授技术资格,提升的节奏之快使许多教师望尘莫及。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陈老师职称提升的是您从民间年画和传统水墨中提取元素进行的当代主题创作“法象”、“天空界”系列,还是您屡屡参加全国重要艺术展览如“中国风景油画展”、“全国美展”、“中国油画展”、“中国水彩肖像展”并多获重要奖项的原因呢?尽管您还出版了三部理论著作,但我想它们和您的当代主题绘画创作并不是起推动作用的因素,确保您获得官方或主流认证的应是您的风景绘画作品。在长期的绘画过程中,您的风景绘画和当代绘画一直并行,即使是您的当代绘画已经在市场上获得充分空间的情况下。于是我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激发您长期保持风景绘画的创作?
陈 流:自然风景和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人文风景历来是云南吸引本土和外省艺术家的优势资源,“风景”也成为了云南艺术在外省艺术家心中的一个主要概念。不管是采风还是猎奇,中国美协每年都要组织一批与云南相关或不相关的画家到云南进行采风。我身在这种风景当中,它丰富的色彩不能不吸引我。
更进一步就要说到我的成长经历了。我生在一个相对保守的家庭,外公是位作家,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家里的规矩很多。我从小就在家中处于被寄予厚望而又不被寄予厚望的状态,因为我的文化课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参加各类儿童美展却总能获奖,家里人便认为我或许会像父母一样成为艺术家,于是便有意将我向艺术的方向培养。而能够获奖也更加激发了我儿时对绘画的兴趣和热情。
初中阶段我才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学习基础素描和色彩。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后,由于学院非常看重学生的技术和技法基础,我就带着成就一手好技法的期待陷入对技术的痴迷状态中。其实相对于中央美院来说,中央工艺美院对技术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虽然我们这些被录取的学生都有较好的基本功,但是入校以后的专业教学很开放。我们学习的课程和进大学之前接触的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先是上了一段时间动物写生课,然后就是进行壁画、壁毯、浮雕的设计,还要学习漆艺、国画和水彩。当时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教学系统,线索不清楚,以我们当时的能力看不懂学校制定这些课程的目的。但我们还是初步形成了一个概念,工艺美院这样做是要培养我们的设计理念,对技术的要求是伴随性内容。这造成我大学四年的认识混乱,只是明白要把基础做好,至于什么是设计和创作,没有形成清楚的概念。
张光华:在这个培养系统里面,您初步形成的设计理念是什么?这种设计理念是否影响到了您今天的绘画语言,诸如您风景绘画中的装饰性语言或壁画效果——块面结构、色彩简洁、肌理丰富是否受这种理念或这个培养系统的影响所致?
陈 流:影响是肯定有的。在大学,我接受的风景训练重在追求一种视觉效果,我不必考虑画的是哪里,不考虑它的地域特征,也不涉及人文元素,在意的是这种画面效果是好还是不好,我自己的审美视角能不能接受。这段时间的练习导致我后面在画面(风景绘画和当代创作)中痴迷于物象的肌理感和其他技术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工艺美院教学方法的影响,我们的专业课程强化培养的是设计创意以及对创意的完善技巧,但是作为一个本课生我们尚没有能力或没有足够知识积累去对自己的创意进行文化元素的剖析和辨别,从而也就影响到创意本身的人文素养,在理念上很难有所创新。
张光华: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大学毕业时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陈 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创作进行阶段。其实我在上课阶段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能力突破它。我的毕业创作持续了半年,在这半年里我一直想怎样从这种束缚中挣脱出来,于是我的毕业创作违背了校方的要求。学校希望我创作一些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唯美主义的作品,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反映我大学四年生活状态的主题。我们上大学时正是中国的机器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作为年青人我们对机器和零件充满好奇和期待,希望自己能够在机械或电子时代有所发展。我创作了一组油画三联画《预言》,在第一幅中,一个男青年被钢筋、电缆等金属束缚住了,非常无奈和无助,作为背景的风景是被解构了的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第二幅,是想告诉大家我很累,活在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时代,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应该把画画好,但仅仅画的好看是不够的,离艺术的理想还很远;第三幅,这个青年决定挣脱束缚跳出去,哪怕面前是悬崖或是另外一个无法轮回的时空,他都要跳出去。画中男人体的造型相对于学院标准来说是很古怪的,不讲求色彩的和谐与稳定,人物的肌体本来已经很怪异了,还在他的臀部画了一小股亮光,就像萤火虫的屁股一样。我也不知道当时这样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很清楚这种表现手法是违背工艺美院的美学要求的。画完了以后我自己是心满意足的,但却令我的导师很为难,尽管我的技法不错,但历届的毕业生从来没有谁像这样画过。庆幸的是这件毕业创作被打了及格分。
张光华:1996年大学毕业后您回到云南并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环境的变化有没有帮助您从毕业前的迷惘和困惑中跳出来呢?
陈 流:1996年到2000年这四年中,我基本上处在一种被束缚的状态中,画了不少水彩风景,这个阶段是促使我真正进入到风景绘画的重要时期。回到昆明后我考察了云南的很多写生基地,包括毛旭辉老师他们常去的圭山大糯黑,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奇异,房屋和路面都是石头和石板建的,村庄的色彩很浓烈,我在那儿画了很多作品。那时我画画是有重心的,我脑中已经对云南风景有了辨别能力,能够清晰的表达它的地域性特征,画得及其丰富、具体。那时多数艺术家的云南风景画相对传统,法国印象派和俄罗斯现实主义风景绘画的特征比较明显,画面有直观的色彩、概括的块面,但不会有太多的细节,塑造手段也比较单一。而我刻意去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表现手法的尝试,说的直白一点,我那时希望让这些画风景或写实风格的前辈艺术家群体知道或承认云南又来了一个技术不错的画家,画得比他们还深入、还丰富,比他们的色彩控制能力和稳定性更强。那四年我一直把这些前辈艺术家当作自己在技术上的假想敌,让他们认可和欣赏自己高超的水彩技艺,向他们证明水彩也可以画得像油画一样,可以比油画画出更多的细节。有点炫技的意思,以此激励自己去超越自己。
那四年我过得很累,因为为技术付出了太多时间,而且为了精益求精我忍痛搁置了我喜欢的其他一些题材。我画了大量很复杂的物象,像热带雨林、结构复杂的少数民族民居,画着画着就感觉到了无聊和乏味。更严重的是,我对这些太过熟悉的对象已经失去了兴趣和新鲜感,再到圭山、丽江等任何一个景点,我一眼就能找到我应该支画架的地方、我应该取景的点、我应该从什么角度画、我应该用什么颜料调多少水会出什么效果,甚至不用到丽江仅凭印象就能在工作室真实再现丽江的风景——不再动脑筋了。
张光华:这似乎映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用四年去验证一件事情总比用四年去附和一些事情有价值。无聊和乏味毕竟只是一种心境,您对这种不再动脑筋即创造力停滞的消极处境的反思或警惕是如何产生的?
陈 流:2000年左右一个台湾藏家来买我的画,他提出的两个问题使我很惊讶。第一个问题是:“陈老师,你们大陆的画家是不是都喜欢画灰色调呀?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处境让你们不开心才导致画那么多灰色呢?”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但事后想想,在中国的学院教育中,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如何寻找和表现灰调子的练习上,用在如何去表现微妙的光影变化,这种模式过多地贯彻在大家的绘画学习中,就使大家的作品很接近,普遍表现出一种弱化的、灰灰的色彩,一片哀伤和忧郁。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原来您不是一位老画家呀?”这个问题让我更加惊讶,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的画画得很老辣,我还以为您是一位老画家于是我就过来了,原来您只是二十岁刚出头。”听他这么说我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后来想想,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的那种心理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我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会执着在和老艺术家比拼的道路上?我为什么要在前人的平台上去挣得自己的位子?结果把自己“挣”成了老画家中的一员,这是挺可悲的。
于是,在2000年结束之前,我就釜底抽薪,把这四年中坚持的东西甩了个淋漓尽致。然而,再一次“物极必反”,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不再画水彩和风景,因为我当时下定决心再也不画了,因为不能让自己沦为水彩风景的写实工具和印刷机。得知这个决定,很多圈子里的朋友劝我不要放弃,但我想反正这种写实的作品卖的价格不高,也不是那么容易卖,那我画什么有何所谓呢?2000年到2005年我就进入到了一个完全自由的创作状态,创作了很多偏向当代绘画的作品。
张光华:您画的是风景作品,而且您的写实能力那么好,您的作品应该很好卖才对,为什么会说价格很低而且很难卖掉呢?
陈 流:2000年以前,云南的艺术市场还没有形成。市场上卖的都是“旅游商品”,虽然有几家画廊,但它们卖的依然是“旅游商品”。我的作品首先在价格上高于“旅游商品”;其次,我的题材不会有意讨好观众;第三,我对市场和那些画廊主也失去了兴趣,喜欢画而又懂一点画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又不买。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境。
张光华:在进入下一个重要阶段之前,我们先插入几个之前未完成的问题。您从小学开始就参加各类儿童美展,您当时选用的绘画媒材是什么?
陈 流:小学时候多用油画棒和蜡笔画画,也做了一些黑白版画。
张光华:小学就开始做版画?这是不是因为您母亲李秀老师的影响?
陈 流:这不能算影响,我母亲也没有刻意教过我做版画。因为我母亲是做版画的,所以我们家当时最多的就是木板和刻刀。我父亲陈饶光老师虽然有油画布和油画颜料,但太贵了,父亲不可能把这么贵的材料交给我去乱涂乱画。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我就只能用木板和刻刀刻版画了,而且版画制作的过程相对较慢,先画一个小稿然后再一刀一刀的去刻,我母亲给我一块板——通常都是她不用的下脚料,我要刻一个星期才能把这些材料消耗掉。
张光华:也就是说您在小学阶段还没有接触油画和水彩?
陈 流:没有。
张光华:您刚才也说了,接触正规美术训练是从中学开始的,你们当时接受的是什么训练科目?
陈 流:我的中学训练很特殊,因为我是和大学生一块儿训练的。从初中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去上写生课,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会把我带去教室,然后把我仍在那儿就不管了。这是一个很突然的接受过程,感觉画画一下子就不再像小猫小狗做游戏一样自在随意了。每天跟着那些大学生画,他们画什么我就画什么,跟着大一和大二的学生画了很多静物和石膏像。进高中后又随着大三的学生画人体。我的基础训练就是这样进行的。
张光华:大学阶段,尽管各个艺术门类和各种艺术材料的混合教学让您感到迷惘,但您刚才说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曾痴迷于对技术的练习,这里所痴迷的媒材是不是和回到云艺后一样都是水彩?
陈 流:在大学重点攻克的是水彩。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学过水彩,因为之前我很惧怕水彩。第一个原因是,我父亲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与他同时来到云南的还有他同学夏斌文,现在中国美协水彩艺委会的主任黄铁山是他们的同班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画水彩。通过看和听这些自己崇拜的前辈对水彩的钻研和讨论,在我浅薄的认识里就产生了“水彩的门槛特别高”这个概念,比如说水彩不能多次修改、不能用白色,看似必然性的因素其实是偶然性,下笔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很不容易修改。另外一个原因是,1989年至1992年的高中阶段我对水彩技法并不感兴趣。因为当时看到很多人制作水彩画效果的手法就是在画面上撒把盐或酒精,有些人所谓的“对印”就是随意在玻璃板上浇上颜色,然后把纸盖上去再拉起来添加几笔,最后签个名就宣告作品完成了。我认为这并不是画画,“撒盐”和“对印”不能完全被主观意志控制,而真正的绘画的技术性要求是很严谨的。
张光华:那后来又是因何而学习水彩的?
陈 流:大学三年级时我们开设了《超写实绘画》。这门课程是由台湾艺术家姚庆章老师引入中央工艺的。这门课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写实,只是要求把对象画得有类似照片的效果就可以了。这在当时对我们是有很大难度的,好在我们大一、大二画了很长时间的工笔重彩,对《永乐宫壁画》、《游春图》等传统写实作品进行了大量临摹,掌握了一些渲染技巧。于是我们在做这门课的作业时主要采用了渲染的技法,先从局部着手,然后一层一层推着走,可以把物象画得很真实。
上完这门课我画的一张水彩画作业竟然把自己都吓到了。这幅画画的是一组冰冻的鱼,画得真比照片的效果还清晰,因为当时的照相机分辨率不是很高,胶卷冲洗出来的效果也不很理想。这幅画花去了四周的时间,但我画出了比照片还要深入的细节,简直是一件用水彩制作的照片,效果太令我惊讶了,水彩可以画出照相写实风格的作品这一发现更使我惊讶。从这幅《冰鱼》开始,我对水彩画产生了兴趣。随着练习的增加,我发现水彩的可塑性真的很强,甚至比油画更能塑造细节,而且水彩不能用白色的理论也被验证为是讹传。水彩的操作平台也很简单,只要想画拿出纸来裱一下铺在桌上就可以画了,纸的尺幅也很便于操作。相比而言,油画的准备和制作过程就要耗时费事的多了。
张光华:既然发现了自己在水彩静物写实方面的特长,那1996年至2000年为何会选择风景为题材并孤注一掷呢?
陈 流:那四年我大多数时间和父母住在一起,接触到的多是父母一辈的艺术家,我能够进行参照或参考的也是他们。他们经常相邀去写生,我就跟着去。哪里是写生的好去处,什么样的风景好画?我能与之交流和探讨的也是这个群体,从他们的意见中做出选择。他们也都对我寄予厚望。我能够做比较的对象或假想敌也就成了这拨儿老画家,于是在那四年中我就成了这个老画家群体中的年青人。我可以把水彩画得很深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的画面的完整性和细节的丰富性都超过了其中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画家的作品。
张光华:在您的“假想敌”中,对您的影响较为重要的是谁?
陈 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198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先后在云南艺术学院和云南省画院工作的惠远富老师,我在高考之前就跟着他进行了一些基础训练,大学毕业后一直与他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我的风景画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早期的风景也是画民族民俗题材。1999年的“第九届全国美展”,他对我的触动非常大。1999年,由惠老师选择地方,他带着我和我的同事张炜到昆明一个汽车报废厂去画风景写生,画那些破汽车的零件。我当时还带着那群老画家的观点考虑问题,对这些破旧的报废汽车能否作为绘画题材持怀疑态度。但我非常尊重惠老师,既然他选择了那个地方,我就相信那个地方有它的价值。我硬着头皮开始画,从宏观的报废厂画到一个残败的发动机,再到被万吨水压机冲压形成的废铁块,画面越来越抽象。
画这几张画时恰逢“第九届全国美展”即将评选作品,我就问他打算送什么作品去参展,还建议他早点回去准备作品。他却很干脆地说,还要准备什么呀,就送刚刚画完的表现报废汽车的作品。他果然送去一件画被解构的报废汽车的作品。他是云南省画院的专职画家,按常规他的作品可以直接入选,但因为他这张画引起了普遍争议——与全国美展要求的主流美术形态相差实在太大,最终被刷掉了。而我从相对理性的角度出发送去的一件画鱼的纸本水彩作品《渔》就入选了。明知惠老师画得比我好而他的作品却不能入选,这就打断了我长期以来对风景画的认识,使我意识到重新思考什么是风景绘画的必要性。
在此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情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也是1999年,一次云南省画院组织他们去中甸写生,回来后大家进行作品汇总,多数画家画得都是中甸的蓝天、白云和漫山盛开的火红的狼毒花,画得很好看。只有他画的是中甸藏民家中洗菜用的盆子、几个土豆和酥油茶,全是静物写生。这批写生作品肯定是得不到多数同事好评的。后来当我去他家看到这批作品时,我被深深感动了,因为我从他的作品中真切感受到了中甸藏民的生活状态。在他画的盆子上分明能感觉到盆底糊着的那层酥油茶的粘糊糊的质感,能闻到牛、羊肉强烈的膻味,强烈到只有捂着鼻子才能看下去。这批作品也没有被选中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
发生在惠老师身上的这几件事,促使我对“风景”这个概念进行转换。我意识到风景绝对不是刻意去挑一个景点,然后再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去抓拍和捕捉它,恰恰相反,是要捕捉常态化的、非常真实的生活情景。惠老师的事件让我不得不反问:他这样一位已经相当成熟的艺术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非主流的路呢?答案是“风景画”中尚有许多我们没有能力或时间去关注的点,这些点有待我们去发现和发掘。我当时已经养成了一些或好或坏地画风景画的习惯,已经程式化了。我就开始试着摆脱这种画风景的状态,然而我既不能看到惠老师这个方向的出路,又对官方的艺术系统不感兴趣,最后就只有选择放弃风景绘画了——这是2000年的事情。
张光华: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您在2000年以后暂时放弃对风景画的追求而进入到了自由创作状态,开始了当代主题绘画的创作。这种转向其实是您在大学毕业创作阶段就奠定的关怀生命体验的实质性要求,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我们做我们想做的,画我们想画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
陈 流:这种尊重生命体验、尊重自由的要求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持续着,但是大学毕业回到昆明以后我不得不考虑现实的生活问题,还要在云南艺术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得不接受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要做得与他们相似,在相似中比他们做得更好,从而确立自己在江湖上的位置。所以我用了四年的时间去苦练技术,并通过炫技去博得更多地认可。庆幸的是我及时发现了自己的无聊和乏味,并尊重自己的心理体验及时打破了这种固执。
张光华:从官方认可的写实风景到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当代主题创作,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来自舆论、市场和学院等各方面压力的?
陈 流:在这个过程中我倒从来没有害怕什么,因为我做事的思路一向都很清晰,我知道体制的底线是什么,我不会去触碰它。至于当代艺术,我对当代艺术的许多形态是比较抵触的,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遭受过政治迫害,我没有这些体验就做不了那种政治批判性的艺术。还有很多艺术家对拿性和隐私做文章乐此不疲,我认为这是一种变态心理。某些现象可能存在,但既然它不是普遍存在的就没有理由成为众多艺术家的普遍话题。我厌恶与自己的经验无关、为吸引观众而哗众取宠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张光华:进入到当代性的主题创作阶段,您的“破碎的天空”系列中依然体现着您对风景的敏感,强调构图的视角和山川的肌理。但整个空间关系又是虚拟的,这种语言特征从何而来?
陈 流:“破碎的天空”系列受启发于我当时经常在玩的一款游戏《皇牌空战》。每天工作结束回到家就已经很疲累了,除画些小稿之外没有精力再去想其他事情,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打游戏。打着打着我发现这款游戏中从高空俯瞰地面时呈现的地面肌理非常独特,这种视角和肌理感是我背着油画箱到处走所不能得到的。
张光华:这种俯瞰的视角一直延续到您后面的风景绘画作品中,俯视也成为云之外您的风景中另一个主要视觉特征。
在您的另一个系列“天空界”中,除汲取了中国传统水墨绘画中的山石树木之外,更主要的是汲取了民间艺术中的“门神”这个形象。对中国传统山水画元素的借鉴是您在大学的毕业创作中就已经使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到您的某种情愫的延续。与此相同,“门神”这个元素与您在2000以前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绘画是否也有关系呢?
陈 流:从中央工艺毕业回到云南以后,我一直对风情画或民俗画带有叛逆心理,如果非要把我的少数民族题材风景画说成是云南风情画(特指商品画),我认为这是在遭受耻辱。“天空界”中的“神仙”其实取材自筇竹寺,原因有两个:首先,小时候父母特别喜欢带着我们到筇竹寺旁边的山上挖腐殖土回家种花,在挖土之前先要到寺庙里休息和参观。那些罗汉的写实性和趣味性使我被深深震撼,人物造像太生动了!父母也会有意无意地把此种风格类型的泥塑给我做些介绍。我从小就对这些泥塑有深刻的好感。其次,与游戏有关,很多人物养成游戏和格斗游戏中的人物设计都源自古代人物题材,穿着古装,握着冷兵器,很好玩儿。看着这些游戏人物,我就想能不能将筇竹寺门口的金刚转化为游戏中的人物,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的空间使他们活动起来。于是我就设计了虚拟的游戏世界,将筇竹寺中的神仙、罗汉、金刚、力士转化为动画形象做进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们也游戏起来。
张光华:您的这种浪漫情怀在风景绘画中也是淋漓尽现,因为纳兰性德最想知道梦里云归何处,徐志摩最想带走康桥上的那一片云彩,云是天空中最浪漫的骑士,而您的浪漫正是幻化在骑士闪亮的长矛尖上。天性的浪漫让您割不断与自然风景的纽带,这是您2003年的作品《翠湖》和《黄土坡》中那广角构图、舞台式的灯光、绚烂的色彩体现出来的。尽管这是三幅有些虚幻效果的人文景观,但它们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乡土此消彼长关系的哲学思考却是真实动人的。
陈 流:翠湖和黄土坡是我在这个城市中最为熟悉的两个地方,我每天往返在画面所表现的三个地点之间。翠湖每天晚上都是霓虹灯闪烁,许多健身者在这里歌舞升平;黄土坡名副其实,太干了,我希望黄土坡能有一个大湖,湖里还蹲栖着几只青蛙。这些场景日复一日的是如此熟悉,年复一年却变化飞快,有时感觉自己就像那只从“破碎的天空中”误闯进来的小昆虫,俯瞰着翠湖、黄土坡、羊仙坡乃至整个昆明,但却看不到自己。
张光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是每个人都最敏感的话题,面对每天睁开眼睛后看到的新的陌生,有人消极、有人乐观,没有对错,只有运动、变化是真理。作为一名艺术家尤其是绘画风景的艺术家,您无疑是幸福的,因为您可以用画笔逼真再现我们记忆中的纯净家园和那永远浪漫的蓝天、白云、旷野。所以,您2006年又回到了单纯的风景。
陈 流:画了《翠湖》和《黄土坡》之后,又勾起了我对风景的情感。2006年我去法国的巴黎艺术城访问学习了三个月,其间除了参观美术馆就是画画,我画了一批以街景、河道、静物为题材的小幅水彩画。这个阶段又唤起了我那种习惯性的写生状态。2006年以后,每年我都会在感到乏味和疲劳的时候去写生一两个月以调整状态,给几近枯竭的创作思维提供新能量。
张光华:2006年以来的风景画以油画为主,这是不是与您的当代主题创作主要采用油画和丙烯媒材有关?
陈 流:回想起来,我的水彩画已经被停滞了十年了,虽然中间也画过一些,但是不够系统。2000年以来的绘画主要以油画为主,但融合了一些水彩画的技法,比如云彩的那种松动和薄透的感觉,就是以水彩技法去刻画的。
张光华:在您的风景绘画中,很好地实现了多种绘画媒介的多种技法,比如说油画风景中有水彩画和水墨画中的留白技法,画面构图中保留着壁画的色块处理手法等,这种诸技法的融合和平衡是如何实现的?
陈 流:我毕竟画了这么多年,对画面的完整性和色彩的协调性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验体系。写生的观察经验能够帮助我在贫乏的角落里找到亮点;从初中开始的勤奋、扎实的基础训练帮助我养成良好的运筹能力;多年的水彩习惯能保证我快而不改。总之,要画好画需要勤奋。
【编辑: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