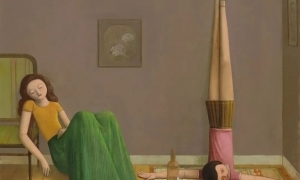当代艺术家 王广义
我站在两种“洗脑”势力之间
大家对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波普”概念有些模糊。今天中国“政治波谱”艺术代表人物王广义老师来到搜狐文化客厅,由他来为大家解释"政治波普"的概念和内涵。
王广义:其实这个词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背景,是评论家和媒体说出来的。作为艺术家,还是做自己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他的工作要有意义,这个是让艺术者最高兴的,其实词汇倒不具有什么意义。
主持人:您的政治波谱创作有几个关键词,"大批判"、"冷战美学",今天新的展览开幕上,又出现非常重要的词:"温度"。这三个关键词连接起来与您作品的脉络是什么样的?
王广义:知道"大批判"的人太多了,我作品中"大批判"的本意是想表达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我们生活的国度为主体的有乌托邦理想的国家,有乌托邦理想的国家对人的影响可以用"洗脑"这个词,它是有通过特定的方式,通过各种宣传让人们去除别的思想,之后你会相信为了乌托邦理想牺牲自己为之奋斗。
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欧美的"拜物教"逻辑影响了我们。它对我们的洗脑是通过商品的设计,让你疯狂购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IPHONE。这个洗脑的强度和力量不亚于乌托邦的宣传画。所以我作为艺术家要把我自己假设是在两个地带中间的人,我的左侧是乌托邦理想,我的右侧是拜物教,我站中间,将这两种洗脑程序重合,这种重合产生的图象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大批判。其实大批判的本意是这个,虽然有很多误解、但误解有助于作品的传播,但是我说的是我真正的本意。
而"冷战美学"我需要找到类似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含义,我们所说的"冷战"其实也是这两个世界构成的相互的妖魔化的产物。乌托邦世界的人和拜物教世界的人对彼此都有一种妖魔化的描述,其实即使到今天这种描述仍然断断续续的存在,但现在情况是,又一种相互渗透的感觉,比如在我们乌托邦的国度里慢慢渗入一些拜物教的精神,在拜物教领域渗透乌托邦的理想,大概是这样。
这次展览我新的作品叫"温度",我想把日常的,我们非常熟悉的物品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呈现出来它们的改变。它和你在商店买的温度计是不同的,因为我用艺术家身份,以艺术的名义将几千个温度计放在展厅里面,它们会呈现真实的温度,而这个真实的温度又不具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价值,只是它在不同的国家展览确实会呈现不同温度,这里面我想会引出全球变暖的事情,以及它背后所隐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制衡的产物。这是我的想法,但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对于我来说不确定的,但我希望人们能从日常事务甚至它的背后思考一些和某些国际政治相关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到了中东、美国或者欧洲展出此作品,它会产生出更加具体的对话,在这种过程中,艺术家的责任是不是把社会政治的话题通过自己的思考直接传递给大众?
王广义:我想艺术家如果能通过自己作品引起观者的思考就足够了。我想艺术家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就是,会在常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一些物品和事物当中发现里面的潜在暗示或者线索。艺术家做的工作应当和人们的生活有关,这种有关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像国际间的权力制衡,事实上怎么运作艺术家也不清楚,只是艺术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这次展览除了作品之外还有一个手稿式的东西,记录了你从89年到现在20年的漂泊的过程。很多人把手稿或者初始的东西遗忘,您为何非常重视这些资料并一直收集?
王广义:应当说这次展览我20多年的草图和方案是最主要的主体:一方面,我看到这20年来自己都想过什么,我把这些清理一遍,发现我自己确实想过很多问题,虽然这里面提供的思想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在我看来倒是有重要价值,艺术家思想不确定性说明思想线索比较多向;另一方面,我在四川美院这个空间来做展览,也是想给年轻艺术家提供一次观看的机会,让他们了解一个艺术家走过的历程,这个历程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有名气的作品,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这些方案草图是一种真实的思想探索历程,如果这个展览对一个年轻艺术家有些用我觉得就挺好。
【相关资讯】
比起社交 重审自己的过程更重要
主持人:这样的展览会给收藏家、观众一个新鲜、立体的角度去认识艺术家。您搜集这么多的生活中的小草图,您是否是一个比较喜欢怀旧或者说有历史感的人?
王广义:作为艺术家的思想线索,我可能是对历史感比较看重。可能别人对这些不知道,但对于我,历史感是很重要的概念。通俗说是因为人不同,其实每种生活都是好的生活,我觉得都一样的,有人觉得在历史这样一个大环境中生活觉得很舒服,有一种存在感,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在片断的生活得也很好,这都没问题。
主持人:我们在活动上很少看见王老师的身影,会不会也有一些人说大牌艺术家都很少现身,您看起来很冷酷又难以接近,但是接触起来又比较随和,这个跟您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吧?
王广义:应当是,我不大参加好多社交意义上的活动,源于各种理由,我有点社交恐惧症。人少点大家聊天我可以非常HIGH,但是人一多就麻烦,聚会一超过15个人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尤其这种社交性的活动端着酒杯,我找不到北,所以说我不大参加。
主持人:您的很多作品被大家熟知,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都会遇到类似转型或者新的发展阶段的问题,现阶段您有没有这样的困境?
王广义:这是所有艺术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他有一部被人所熟知的作品,人们想起你的时候就会是那件作品。但艺术家也要往前走,最起码要做新的东西,这是个特别煎熬的事情,这个煎熬时期的长短取决于偶然间某一个词或者某一个事物突然点燃你的感觉,艺术家这个时期是很难熬的。
现在这个时期应当属于我在思考我所思考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我想过所有问题,它的价值在哪里?我现在想这件事情,包括我做这次展览将所有的草图列出来,我在整理它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把整个脉络理清。我对一件事想了20多年的结果就是思想的痕迹,我现在看它是否有价值。艺术家有时会想,我把一生投入这件事情,自己还一本正经在做,并且想了很多,但是它是否真的有价值,这个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这个不是别人说的。
主持人:在做的过程当中不会特别去这样?
王广义:在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在特定的年龄段,比如30岁左右的时候你是不会想的,那时候成功作为一种动力,想的就是:我做东西,要引起人们重视,要吸引人。所有艺术家都这样,到一种阶段会思考他所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这和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成名都没关系了,因为功名是社会性的描述、是媒体的描述,我想艺术家到达一定年龄就不会这么肤浅地在意这些,而是会思考一件事的价值。其实自己在内心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会特别从容,如果自己没弄清楚,自己对自己所做所有事情没有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会很慌的。
主持人:您不太认同媒体的传播吗?
王广义:不是的。所有的艺术家都感谢媒体传播,但是媒体传播有很可怕的东西,它会把艺术家所有的话语改变,最后弄出一个片断的东西给人们看。也许艺术家在这之前说的某一段很有意义,但媒体没采纳,但这个艺术家突然说,"艺术这个事挺烦的",其实这句话完全不在采访范围内,但是媒体会这个放上去,完全不考虑语境。所以我现在尽量遏制住这些话语。
“艺术产业化”很邪恶 摧毁价值观
主持人:在二三十年前,您只有50块或者几块钱的时候也在坚持做艺术坚持画画,现在更多的说法是做艺术需要更多的财力和资金的支持才能传播包括发展空间更大。
王广义:我觉得艺术产业化这个词汇确实太邪恶了,这个词汇把艺术完全放在脚底下。我觉得艺术自身一定有真诚的东西,更主要艺术产业化这种想法、这种传播会毁掉很多年轻艺术家,让这些艺术家觉得艺术是这样的事情,这个很摧毁人。
主持人:村上隆的讲座无论在川美还是央美都是爆满,学生对于与品牌与时尚的艺术产业化的合作非常有兴趣。
王广义:有些人有兴趣,但对我而言,我用觉得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这个邪恶的词会构成诱惑,它会摧毁价值感。
主持人:艺术产业化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词,村上隆又是在这上面走的比较远的一个领头羊,村上隆会不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人?
王广义:对他本身倒无所谓,我是这样看:你想怎么做都是可以的,出于你的意愿,怎么都可以。但我觉得在大学里面谈艺术产业化很不好。这个词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邪恶的概念,邪恶是构成诱惑的,艺术产业化最早从英文里面出来,创意文化产业大概是这个概念,那天重庆记者问我建立艺术园区,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太可怕了。艺术还是回到最简单的东西,你热爱它你就做,其实社会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艺术创意产业太可怕了,变成养殖场概念了。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