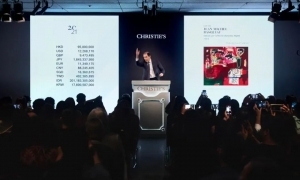画坛雄狮石虎
正如非洲草原上的雄狮,自它降临的那一刻起,它的使命和尊严应运而生,一生相随。石虎似乎也是为画而生的,时代选择了他发言和嘶吼。要不然,我们真的难以理解,这个出生于素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河北徐水农村的孩子,如何因缘际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成为了中国艺术新潮的前行者、八十年代成为了艺术创新的盗火者、九十年代成为了艺术市场的领军者、新世纪成为了传承薪火的独行者。
一路走来,在当代艺术的每一个历史节点上,石虎都以他前行一步的敏锐和创作实绩成为后行者的参照和标尺。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无论沉潜还是奔腾,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石虎的人生和艺术都与中国当代三十年的艺术运动和潮流息息相关。他的存在不仅仅具有见证者的意义,更是当代美术发展进程中不可忽略的环节和深度。他的艺术不仅拓展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界,赋予绘画一种全新的视野,更以实质性的改造和尝试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这个角度去认识石虎,我们拥有的才不会仅仅是惊讶、好奇、猜测和臆想,而是一种事实的判断和尊重。
如果从1978年石虎非洲写生算起(当然这个时间节点还可以前移),历经三十余年,石虎的创作完全算得上超重量级。创造了多少作品,恐怕石虎自己也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这种量的积累不是单一图式的重复和叠加,它是不断创新、尝试和突围的集合。在他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创造力、创新力、辐射力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
面对他不可胜数的作品,我们大体的感受如同一滴墨落入水中,幻化万相,无所从来,有种无法定焦的焦虑和疑惑。但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在更大的时空跨度内把石虎的艺术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谱系中,就能比较清晰地看出石虎艺术的源头和奔流轨迹,也能比较准确地对石虎艺术的价值做出合理判定。
去过黄河、长江源头的人都会惊讶的发现:这两条伟大的河流源头竟然是泊泊清流。回溯石虎艺术的起源,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发现:构建石虎浩瀚艺术的源头并不出奇,在他的童年和早期作品中就已显现,那就是:民间艺术、诗歌传统和他独有的禀赋。
画坛雄狮石虎
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之核中最重要的“铀元素”,也是中国艺术现代主义进程中最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在无数卓有成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上都有体现。石虎出身于农村,童年在农村度过,民间艺术的吊纸画、纸灯笼、剪纸、绣花鞋等等成了洞开他艺术心灵的星光。后来他虽然上过美院,但却是以工艺设计为主,他最初从事的职业也是与工艺、雕刻有关。这种起于童年,类似白纸上的刻印和本真成为石虎艺术的一个烙印,在他以后多变的艺术风格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从这一点上讲,石虎的艺术是有根的,无论他以后成长的枝叶如何茂密,枝干如何伸展,果实如何丰硕,他的根系都深深扎在中国民间的土壤上。
而比其他农村孩子幸运的是,石虎有一位上过中法大学、深谙古典诗词的父亲。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是深远的,不仅入骨地影响了石虎未来的艺术和思考,也从禀性上锻造了一只幼狮健康激越的品格。这是一种典型“中国式父亲”的教育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知名画家无不是以诗书画融为一体的,石虎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在时代的断裂和隔阂后再一次扬起了这面旗帜。联想到当代中国画家能诗能书能画者几近廖廖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说,石虎的这一继承全美了他的创作。在石虎的诗书画体系中,诗又成为他艺术的核心之铀。他不但爱诗,写诗,出版过诗集,还成立过石虎诗会,引来众多当代重量级诗人、诗评家关注,在当代画家群里几成异数。而诗对他书法、绘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书法中,以字为意象的现代书写有着明显的诗意构造,包括他后来引人注目的《论字思维》《字象篇》等著作,也与这种对古典诗词的喜爱有种内在的联系。而他的绘画作品中,仅简单的从作品题目观察,就能洞悉他多变的艺术形式后面蕴藏着的古朴而唯美的诗情画意。
虽然以上的两点至关重要,但石虎之所以成为石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与生俱来生有的一颗如雄狮般“勇敢的心”。美学家高尔泰称之为“具有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石虎颇带传奇的经历也可以证明,他不光有敏锐、深沉、洞达,敢于自我否定的哲学之思,更有勇敢、果毅、坚定,敢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之实。不妨推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 1978年随中国非洲考察团赴非洲13国考察的石虎,不可能把一种发自本能的激情和对艺术的热忱以超越时代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也自然不会有他的作品集三天售出一万册的奇迹。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石虎不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北河西走廊写生时用光脚蘸墨在宣纸上涂抹,被当时保守的老一代搞艺术的斥为胡闹,而自外于体制。在这一点上,石虎就像一只青春期的雄狮,好奇、勇敢、冒险、敢为,喜欢流浪和漂泊。但这是一种力量的积蓄,而不是玩耍和简单的游戏,因为它肩负使命,深知自己的前行方向。正是石虎的这种性格,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率先燃烧了,他的《非洲写生集》成为了一代艺术人的记忆和定格,成为了一种艺术创新的启蒙和信号。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成名后敢于丢掉旧有的风格,大胆吸收西方艺术抽象、构成、色彩等新要素,以特立和独一为画坛瞩目,与周思聪、袁运生等成为文革后中国美术当代化进程中的领跑者和开拓者。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盛名之时离开国内,在一种内心的寂寥和清冷中创造了海外市场的画坛奇迹。也正是这种性格,在国内艺术家对海外市场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又放弃了海外事实的物质和地位尊崇,于新世纪之初回到国内开始了他隐士般的生活。这一次回归不仅是身归,也是心归,是他艺术之命运的需要,也是他自身性灵的渴望。对一只征战多年的雄狮而言,这一次回归不仅是叶落归根式的情感归宿,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国艺术之根的牵挂和眷恋。与其说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从母语出发的新的探寻。性格即命运,石虎的艺术成就与他的性格深度契合。
画坛雄狮石虎
事实已经证明:正是这三个支点有力地撑起了石虎艺术的平台,给了他天马行空的疆域。从此不论他纵横驰骋,还是茕茕孑立,还是游离远行,这种源于身体的温度和血脉中的热度都成为他艺术远行后最深的牵挂,具有着地心引力的作用。这也正是一头雄狮的命运:幼年的种种磨砺都成为他未来成长和征服的本领,但不论你开辟多大的疆域,不论你多么喜欢冒险和远行,你总要回头,因为守护家园是你生下来就必须肩负的使命和光荣。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看石虎的艺旅,会惊奇地发现石虎的出走与回归其实与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探索之路惊人暗合。对西方美术的吸收和借鉴,对艺术市场化的赶潮和审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再认识和回归,石虎的艺术具有十足的历史样本性和跨度感。他的艺术既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离开了这个背景,石虎将只是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如同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再强壮的雄狮也只是流浪者。基于此,探究石虎的艺术才能让我们更加一步地看到了石虎的光焰和使命,才能明确一个画家与时代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才能品味一个画家在时代中的错位和背离,怒放和颓败,也才能更好的认知一个画家在他的时代能释放的能量和所起的作用。
石虎诗、书、画齐擅,但是从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和事实而言,石虎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位为一名画家,一个现代水墨画家。在画家这个点上,诗与书就成为一种潜在的营养和背景。而考察石虎的画,就成为近距离阐释石虎艺术的门径。
好的艺术总是给后来者提供无数的视角和思考,好的画家也总是一人千面,值得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石虎是个多变、多元、多维度的画家,他不断在突围,不断在改变,不断在自己风格趋于完善时否定和升华,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跌宕和不确定感。这显然给近距离解读带来很多困扰和麻烦,但这也正是他艺术的魅力所在。
仅从画面的整体感受而言,石虎的作品画域宽广,奇诡多变,既有民间元素,又有现代乐感,这与石虎的诗歌底色和艺术追求有关。他的重彩作品尤如交响乐,多声部合奏,气势恢弘,充满了生命的激越,但局部的细节又宛如颤音,既有“银瓶乍破水将迸”的激越,又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而他的水墨人物则更似随性的内心吟咏,忽高忽低,忽起忽落,完全是一种即兴的触发和生机。在玄奥的画面构成语言之中,石虎其实给读者留下了可供辨识的空间。
总体而言,画面中的石虎是偏于感性的,现实的关照和内心的涌流都会在瞬间跳荡在画面上,既无成法亦无定规,最丰沛而饱满的只是一个闪念的生成和蔓延。但是越过形式的玄奥,又会觉得画面后的石虎是偏于理性的,他有自己独有的创作理念和一套较为完备的创作体系。我们会发现石虎的变化更多的是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和造型的改造,是对画面构成语言的破立和形式意趣的拓展。穿越这些变化的迷雾,其实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石虎有内在比较稳定的艺术抱负,那就是对中国艺术道性的追索,其实是一种回归本源的向往。这是石虎基于对华夏文明的雄强之风、字与诗所释放的无形之美、民间艺术的率朴之气、传统水墨的品质标准多年思考与实践的体味和认知,也是他一直强调的“文化根性的信仰”。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条精神主线,所以不论石虎艺术形式的探索如何前进、迥回、曲折、散放,我们都能从“写实写意、重彩淡墨”这样一条小径走入石虎的艺术王国去漫步和徜徉。
写实:这是七十年代后画家无可选择的基础和原点,既是一种技术要素,也是一种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既是一个核,也是一个壳,如何对待写实其实是当代画家都要面对的课题。以画家周思聪为例,当她创作《矿工图》时,写实已无法表达出她内心的动荡与情感,所以必然走向了抽象。与周思聪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创新代表人物之一的石虎,也异曲同工地走上了这样的突围之路。石虎更早期的作品无缘得见,现在偶尔能看到的石虎七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写实仍是主线,题材多以边远山乡和民间素材为主。可以想见,这时的他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喜欢以跋涉的方式寻找扑面而来的感动和激情,强调的是刹那的激动。这种即兴的表达方式在他非洲写生时达到一个高峰,人物写生既造型准确,又有些夸张变形,所以成为七十年代末渴求变化的年轻艺术家竞相学习的模板。但写实完全不能满足石虎内心无法遏止的澎湃激情,只有变形、夸张、抽象似乎才能让人从多年循规蹈矩的窠臼和禁锢中解放。于是在他的写实作品已得到众人的认可和赞誉中,石虎完成了对写实的突破,冲刺到了形式构成的道路上。这既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也是那一代画家渴望打破一统,追求自由表达,寻找多样化的一种自然呈现。只是石虎走得更坚决,更快,更有代表性而已。
画坛雄狮石虎
写意:写意其实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灵魂。但在为现实服务和借西画以改造中国画的时代风潮中,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失落了,变形了,扭曲了。这正是石虎近年来带有些控诉式的反复强调中国画灵魂性的精神的源由。可以看出,从写实到表现再到写意,石虎的良心一叹也是源于自身实践的。从写实的禁锢中突围之后,石虎的作品最初注重的是作品的表现性。不能否认,这与当时借鉴西画的风潮有关,也与石虎自身寻找变化的内在需求有关。这些具有表现性的作品介于写实与写意之间,形式感的变化之下承载的主体已不是实相,而是生命的直觉、灵与肉的挣扎,形式美感的眺望。若即若离,恍兮惚兮,玄奥多诡,不可名状,由实而虚,由写到意,放达恣肆,一任自然。既有强烈的西方形式语言,又有浓郁的中国工艺特色,更有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韵致。此时正是八五新潮美术兴起之时,石虎的探索符合时代的冲动,又一次成为渴望打破成规、走出陈式的典范。而石虎世纪初回归国内创作的大量水墨作品已完全进入写意范畴。这种过渡贯穿了石虎的经历和创作,对这个时代的美术动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照系价值。
重彩: 重彩画的出现与其说是中国画工具材料的变革,不如说更是改革开放后国人心态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形式化、色彩化、物质化过渡的一种审美需求。它依托的是大国崛起后对富丽堂皇、大国气象的诉求。但是石虎的重彩作品显然超前并迥异于这种时代风潮。石虎上世纪90年代移居澳门,浪迹异地的孤独感和城市景观的刺激,以及他内心强烈的形式表达都在重彩领域绽达到了淋漓尽致的辉煌。作为一只正当盛年的雄狮,此时的石虎以重彩作品实现了自我的精神加冕。这也是一个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集中释放的疯狂期。开放的视野与内地迥乎不同的生存环境似乎赋予了石虎艺术一种魔力和迷幻。这一时期的作品宏大而灿烂,去国后的思乡之情,现代都市的迷幻魅影,独处高楼的孤独愁怅,加上东方原始的风格符号,西方平面分割和抽象要素的集合,重彩的冲击和暴力,呈现出动态、多变、拙稚、奇幻又不繁复的动画效果。石虎在艺术上的实验性至此达到了一种边界,也形成了极具东方特色的个人图式和视觉图像。这一时期石虎在海外的大获成功更多的是视觉方式和表达形式的新奇,他以自己的方式把东方风格进行了新异的解读。
淡墨: 之所以说是淡墨而不是水墨,正恰在于和重彩的对比,一重一淡之间,一去一回之中,石虎的艺术多了些转折和迂回,也多了些意味和趣向。相较于重,淡是一种回归;相较于彩,墨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不仅表现在石虎重新回到国内生活和创作,更是在艺术语言上进行再构和整合的旅途。这是一次远行后的梳理和回望。这一阶段,石虎虽然不时仍有重彩大作出现,但他的艺术核心却放在了水墨意象的追索和探求上。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他一系列理论的积淀和主张。他的字思维、字象篇、笔篁篇、神觉篇以及从母语出发,画不会画的画等艺术主张开始发酵,逐渐涉及中国画的意义在哪里,中国画的方向在哪里这些原初的命题。这种追问在当代美术视海外资本青睐为成功的功利背景下,以西方美术观念作为作品标准评判价值的学术幻像中,再一次成为中国艺术自信心从何而来的时代强音。这种发言与他1985年的《蛮梦》可以对比,精神强度完全一致,而后者更比前者多了一分自信和清醒。雄狮归来,不再是年少时的一味霸悍和旁若无人的生猛,而是多了份中国传统文化的智识和安然。石虎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未被展开的文化。而这种展开当然有待后来者的体认和开拓。
这一时期的作品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灵魂的冒险。曾经沧海的回望和对当代艺术虚假繁荣的失望使石虎不在安于自身灵魂的妥贴,他又一次自觉站在了时代的前列,重唤失落的传统和精神。他画的水墨人物,纯以裸女为对象,但着力点却在水与墨的关系、线与形的变化上。画作似乎变成了线条的游戏,水迹墨线幻化万千,不知从何而来,又到哪里而去。这种种尝试我都看作是石虎对中国水墨画基本要素的一种重新构建,是对骨法用笔和传神写意的个人阐述。从重彩到水墨,他的画从繁而简,水墨人物和布本赋彩作品人物虽有抽象、更叠,但画面语言却是明晰的,线条再一次成为了主角,却脱离了书法一波三折的肯定而走上了线条缠绕回旋的不确定性,有种金属的质地感和舞蹈中长袖翻转的立体感,给读者的审读空间更大了,对道的追问成为了画外之旨。留心一下他画的水墨人体作品的命名,比如《来云朵话》《蝶飞草碧》《问梦香云》等等,原本熟悉的字在石虎重新排烈之下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却又分明深具古典韵律之美。这种打乱秩序的并置和交叠不仅表现在文字上,也在他的艺术上成为一种石虎式的标志。作为一个人物画家,近两年石虎又创作了一系列水墨山水画,与传统山水画不同的是,这些作品似乎仍然是人物画的延续,是以人物画的构架对山水画进行重新构造的过程。这种种越界的搭配和尝试为石虎的艺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危胁,创作者容易进入一种无法而法的惯性冲动之中,而欣赏者也往往会在一种过度的想象中迷失和抵触。
奇中见奇,险中造险,这就是石虎的艺术带给读者的新鲜和活力。
魂归来兮。
我在我生命气息里寻找着朴释艺术的真义”。
“瓦、瓮、瓢、锅,那里香留着我的青心和爱永”。
在中国传统文化已然断裂的当代,在中西文化交叠中国人文精神式微的今天,在中国艺术大步迈出国门又不知走向何方的时刻,石虎又一次以个人的方式投入新的战斗。尽管这本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战斗。
这就是石虎作为一只雄狮选择的方式。他永远不会为世俗的不解、嘲笑、敌视而停下脚步。他喜欢漂泊、游走而不愿意在一个地方被人称王。他宁愿怀抱勇敢的心奔入另一场战斗,也不愿意成为困境和安逸中的百兽之王。
但事实是,他的王国已然建立,他的艺术价值早已昭然,而这份荣耀并不因为人生渐至夕阳而呈现老态,反而成就了一段不老的奇迹。
这是艺术赋予他的光辉和恩典,他受之无愧。
【编辑:田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