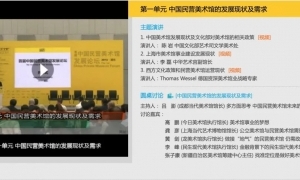今年12月,在经历了几个月由新冠带来的艺术世界动荡变化之后——包括本周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in Miami Beach)的取消——一个新的体验式艺术中心即将在迈阿密落成。该中心是 Superblue 工作室经手的第一件作品。Superblue 脱胎于佩斯画廊(Pace Gallery)的 PaceX 项目,目前以完全独立于画廊的形式运作。
这座占地5万平方英尺的建筑位于阿拉帕塔(Allapattah)社区的鲁贝尔博物馆(Rubell Museum)对面,将展示 JR、里奥·维拉瑞尔(Leo Villareal)和尼克·卡夫(Nick Cave)等艺术家的大型装置和行为艺术,并且拥有足够的空间同时举行多个艺术项目。与以往不同的是,该中心不以销售高价作品为主要目的,而是主要专注于门票的销售和艺术作品的委托,这也是画廊和相关企业历来没有充分利用的商业领域。此举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可能性,不仅是佩斯长期以来推动体验式艺术发展的结晶,也顺势开启了艺术史的新篇章。

曾担任佩斯伦敦(Pace London)总监的莫莉·登特-布罗克赫斯特(Mollie Dent-Brocklehurst),与佩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共同创立了 Superblue。她指出,佩斯画廊很早就与罗伯特·欧文(Robert Irwin , 1966年开始在佩斯展出)和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 2003年首次在佩斯威登斯坦画廊【PaceWildenstein】展出)等“光线与空间”艺术家展开了倾力合作。这些艺术家是佩斯目前代理的一长串体验式艺术家的先驱,其中便包括 DRIFT、teamLab、Random International、拉斐尔·洛扎诺- 亨默(Rafael Lozano-Hemmer)和里奥·维拉瑞尔等广受欢迎的大型作品艺术家。登特-布罗克赫斯特特别指出,过去十年里特瑞尔日益增长的人气,成为了体验式项目不断壮大的基石。
登特-布罗克赫斯特表示:“继古根海姆展之后,詹姆斯·特瑞尔的追随者在过去10年里持续增长,观众群也越来越大。” 2013年,特瑞尔的作品回顾展横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和休斯顿美术博物馆(Museum of Fine Arts)。“现在,随着展览遍布世界各地,他的崇拜者也越来越多。这显然不是在10年内才发生的,人们对他的狂热历时已久。特瑞尔人气以指数级蹿升,并非凭空出现的奇迹。”
据2013年帮助策划特瑞尔展览的古根海姆策展人纳特·特罗曼(Nat Trotman)所言,那场展览本身见证了当时艺术潮流的顶峰。2000年开始,公众对互动、体验式艺术兴趣的不断增长,最终促成了展览的成功。

“很明显,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但在千禧年早期,确实发生了一些事——艺术作为一种社会体验开始变得更加有趣,”特罗曼说。“我认为这与消费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趋势紧密相连,但也与技术、智能手机,以及被社交媒体所过滤的世界体验息息相关。这导致了人们更为关注转瞬即逝的、在场的艺术体验,对行为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当年,古根海姆的特瑞尔展在纽约无出其右,每天吸引的参观者比其他展览都要多。据特罗曼的分析,此次展览落在了所谓体制化体验性艺术编排(institutional experiential art programming)高潮的末期,其高峰期位于 2005年和2015年之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互动性展览在2010年代中期之后便对公众失去了吸引力——它们只是不再被视作某种奇观,而是渗透到了大众意识中,成为了稀松平常的节目。
特罗曼表示:“互动性渗透了艺术界和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类似提诺·赛格尔(Tino Seghal)的展览,或是詹姆斯·特瑞尔入主古根海姆圆形大厅一类的艺术大事件并不常见,在艺术史上也不甚突出。与此相比,你看到更多的是愈发小巧灵活的瞬时性艺术体验,它们正在世界各处不断涌现。”

到了10年代的后五年,越来越多的体验式博物馆展览开始注重结合更广泛的文化符号,其中就包括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举办的比约克交互式回顾展,以及由导演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Alejandro G. I?árritu)在洛杉矶县立美术馆(LACMA)举办的概念性 VR 展览。大约在同一时间,对沉浸式和互动式体验的需求也催生了众多商业“博物馆 ”,提供“上镜”的艺术体验。冰淇淋博物馆(Museum of Ice Cream),以及像 Artechouse 这样的科技艺术组织就是很好的例子。
特罗曼解释说,这种转变是艺术界经济大潮变化的一部分。由于附带的表演者和技术方面的硬件要求,体验式艺术往往需要策展方投入更多的资金。无论是特瑞尔这样的博物馆展览,还是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和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等艺术家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涡旋厅(Turbine Hall)举办的雄心勃勃的项目,都需要馆方大量的投入。特罗曼表示:“实话实说,艺术机构并非艺术界的经济中心。”对于各大机构而言,定期举办规模宏大的体验式展览实在让人有些捉襟见肘。随着体验式艺术在艺术机构中越来越罕见,这些项目和艺术家们在手头更为宽裕的画廊界中找到了新的归宿,其中以佩斯最为突出。

2016年,佩斯与 teamLab 合作,在其门罗公园画廊(Menlo Park)共同举办了名为“体验数字空间与未来公园 ”(Living Digital Space and Future Parks)的展览。日本艺术团体 teamLab 将光、声、屏幕作品和虚拟现实融入到了一个沉浸式的多房间装置中,成功打破了参观人数的预期。
在展览期间,登特-布罗克赫斯特也开始从总监的角色中转型,更加专注于 Future/Pace 项目。该项目从2016年持续到2018年,由佩斯与文化造景机构 FutureCity 合作运行。她表示,虽然像欧文(Irwin)和特瑞尔(Turrell)这样的艺术家确实奠下了佩斯对互动性萌生兴趣的基石,但“体验数字空间 ”展览才真正进一步催化、扩大了佩斯对体验式艺术的关注。在展览之后的几年里,画廊开始逐步代理如维拉瑞尔和 DRIFT 一类的艺术家,也通过 Future/Pace 项目,呈献了设计二人组 Studio Swine 等人的作品。
“这是另一种吸引参观者的方式。交互是一种体验——身处其中,人们是参与者,而不是观众,”登特-布罗克赫斯特说。“如果你真的走进画廊看一幅画,不仅会真实地看到这幅画,也会不可避免地步入一个销售的空间。但在这类交互展览中,人们并没有这种感觉。参与者大多觉得自己是体验的一部分,没有特定的诉求。”

这种新型的体验也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可能。“体验数字空间 ”展览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宏大、以科技为核心的装置,还在于佩斯“卖票入场”的商业策略。这与画廊的标准做法完全不同,打动了许多参与者。在2019年接受 artnet 新闻采访时,格里姆彻表示,通过买票获得体验是体验式艺术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转变也为新型的赞助和艺术资助形式提供了展示的窗口。
“现在,普通公众是不能直接向艺术家付费的,”他告诉 artnet 新闻。“他们付钱给艺术机构,而体制化的机构则由超高净值的人士赞助支持。它们把有钱人的艺术带到一个大家可以参观的地方,以换取少量的捐款。艺术家和公众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TeamLab 团队自己创立的博物馆以及临时装置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新商业模式潜力的最好典范。其沉浸式的东京空间在开幕第一年就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单一艺术家集中地,总参观人数达230万。

Superblue 兼顾了体验式艺术在策展与商业两方面特有的可能性,将体验式艺术能够为观众提供的直接社会联系,与更为直接的经济赞助形式相联结。在2018年 Future\Pace 项目结束后,登特-布罗克赫斯特过渡到 Superblue 的前身 PaceX,开始广泛招募艺术家。佩斯与特瑞尔及 teamLab 已然建立起来的联系为项目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但登特-布罗克赫斯特很快就超越了画廊既有的名册,引入了 Es Devlin、西蒙·海敦斯(Simon Heijdens)、Studio INI 和 Jacolby Satterwhite 等艺术家和工作室。然而,最终的重点还是落在参观者身上——佩斯致力于创造特殊、个性化的艺术参与,这也是特瑞尔和 teamLab 的装置作品吸引众多观众的原因。尽管目前室内体验因 COVID-19 而存在潜在的风险,但登特-布罗克赫斯特对 Superblue 的未来仍持乐观态度。
“我希望,Superblue 能为更广泛的受众打开大门,”她说。“我们希望吸引一群对艺术一直颇感兴趣,却不太可能前往画廊的人——那些对音乐、时尚、设计和电影感兴趣的人。我们与观众的联系非常广泛。我们甚至还对家庭敞开大门,欢迎那些对艺术体验感兴趣的人,也想与对振奋人心、拓展思维、让人有所收获的事物神往的观众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