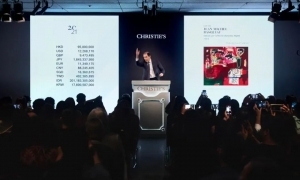栾小杰
栾(栾小杰):你对我现在的画是什么感觉?
林(林善文):我觉得现在有些沉重了,人物无精打采,闭着眼睛,半休眠状态?
栾:恩,半休眠状态。
林: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许活着,但是是一种睡眠状态。我觉得稍微有点沉重。
栾:你觉得沉重?我没觉得沉重啊。
林:那他的选题是什么呢?休息?
栾:也不是,是原来作品的延续。
林: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栾:名字还没有想好。
林:有点像“断背山”的感觉?
栾:也不是,我觉得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是离自己最近的时候。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形式。画中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跟自己在一起的一个人。
林:这样很写实的场景说是一个人,有点说不过去,他太具体了,我体会不到另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时空的感觉,会觉得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当中的两个面。除非像漫画惯用的手法一样,画一个圈,框子里跑出来一个人。那种是常见的叙述方式,对不对?如果五官很明确,也可以明确的把他处理成是他自己,是同一个人。但是,现在从五官上看的话,我不能很明确的看出来是一个人。
栾:能看出来的嘛。
林:真是?反正有一点不确定。从我个人理解上,我会接受他们是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理成同一种发型,穿一样的服装,从发型和服装、表情中出发,理解成他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你说他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你不用另外一种颜色作出一些区别,可能这样更加容易说明?
栾:颜色单一,我是想简单到黑白灰的这种关系。没考虑太多,回到绘画最基本的元素上去。
林:从画面上讲,造型和构图都很经典,也很好看,很抓人。从视觉效果来讲,是很抓人的。从观念的层面来讲,我们就可以讨论很多。
栾:对。
林: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质疑你陈述的是什么。但是从画面来说,传递的情绪一眼看上去就很抓人。
栾:你要说起沉重的话,是有一点。因为我在整个绘图的过程当中,当我画出这个小稿,就是有一种人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我认为成就自己的方式只有靠自己来成就。当心灵得不到另外一种慰藉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画面,我的出发点,还是有这种意思的。
林:你早期的作品“大男孩系列”,人还在动感当中,还在玩当中。“他”虽然跟外界没什么联系,但有种自娱自乐的感觉,他还是很开心自足的。他可能有点自闭,但是他还在玩一个游戏。而你现在这个阶段,人物瘫软,撞墙啊什么的,有点--他要找到依靠。
栾:就是一种虚无的感觉了嘛。
林:对,就是非常虚无。
栾:出现了这种情况。
林:这种情绪上有点,非常的。你的这种方式,我想象一下,我想到《马拉之死》,其实非常相像。或者说像周向林画的刘少奇《1995年1969年11月12日·开封》,马晓腾画的《鲁迅之死》一堆人围在边上。是吧?这件作品有点这种感觉。
栾:对,你说对了。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马拉之死》。嘿。
林:对啊,所以我觉得有这种通感。我看很多人画,再比如伦勃朗的《解剖课》,我就想到相接近的画面,有一种共通的绘画理念。你在画面中的色彩处理基本上是很接近那种气息。是吧?
栾:恩。
林:人物很硬,不松动。如果人物中的脚蹲起来,或者手搭着,感受又会完全不同。这幅画你画的人物有点紧,把他拉得有点僵硬的感觉。但这可能就是你的特点,比如脚的造型,跟真人的脚是有差距的。所以从画面的处理来讲,他更像一个物。“他”不是一个人的概念,而是一个物。
栾:对。
林:一个本该鲜活的人你把他还原到像一根木头一样。他是活着的生命,但是其实他已经死掉了,精神上的死亡。
栾:我已经反过来了,是吧?鲜活的东西变得像个物来对待。
林:你把人当物来看待,你是想表达情感和生命都凝固掉了的一种感觉。是吧?相对而言,如果你要拿这种状态来对应今天的80后或者90后的这种生存状态,很接近,我觉得很接近。很接近这种迷茫。
栾:我这种语言不时尚,不流行。
林:你非常古典,以非常古典的方式来表达。
栾:但又不是纯粹的古典类型。
林:对,很有当代的形式感,他超越了以前的那种繁琐,简约,有极简主义的特征,是当代艺术的语言面貌。从语言上,我觉得这种几何形体其实就是现代语言或者后现代的一种话语方式。所以你的作品放到欧洲的博物馆去,也还是很另类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觉得不快乐,那个画面不快乐。
栾:哈哈。
林:自己没法娱乐自己。
栾:把一个东西消减掉,踢出去。时间一长,自然就回到了这个上面。
林:你05-07年画的“浴缸的系列”(大男孩),他还是有那种鲜活的气息,有水的温度,有那种活的感觉,也许水很冰冷,那种冰冷感觉,主角有想冲破禁锢的感觉。
栾:你说对了,他的思维方式很怪。有时候脑子里面会产生浴缸,但是我那个浴缸已经破碎了,水已经流淌完了。没有水了,干枯了。
林:你就是把水抽干了。特别是躺下来的这个人,你会感觉这个人有气无力。很虚无,这个他感觉已经快断气了。静态的人物,感觉他是睡着了,如果你去题目《睡》,那他就是睡着的状态。那如果你说《Die》(死),他就是死了。就是看你的本意了。
栾:是什么名字就是什么方向。
林:对,作品名可以直接的宣判他在干什么的状态。
栾:我的创作本来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但是画出来的作品,传达出来的不是由我的意志来转移。
林:我觉得好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环节,就是很讲究画面的构成感,绘画首先是色块,以罗斯科抽象画为例,一块或者两块颜色分割大概的形体,再到蒙德里安的那种,由几块颜色组成。从你的画面看很讲究,哪怕那是一根烟(人物的腿),他特别像一根烟(对不起,我脱离了你的本意),我也觉得是很牛的画。用你的办法画一个烟嘴,一样传达出那种让人怎么样的那种情绪,相信你的画面构成感一定是很抓人的。如果是别人,没有这种形式感把握,他不会那么好看。画到这个造型的时候,你已经简约到太像一个物了。是吧?
栾:是,你的感觉是很对的。我一直想画人体,就是纯粹的那种人体。我画画是比较理性的。
林:你在玩味造型?
栾:对,所以说我也没有觉得画得有那么苦。
林:就作品的主题而言,你可以让你笔下的人物快乐、忧伤、痛苦、沉重,你都可以。但其实在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是快乐,是方力钧和岳敏君作品的那种笑。
栾:没有办法,我是背道而驰。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从众,反着走。
林:对。
栾:这样非常吃亏。(笑)
林:不畅销,因为这只能自己面对,不能分享。不会有人跟你说:“我来跟你分享我的痛苦。”这个只能独自面对。而笑脸就可以挂在餐厅里面,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可以很开心。但是你这个挂到餐厅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画会让你一下子没有食欲了。
栾:按道理来说,都应该有快乐的一面。
林:对,我觉得你应该有这个阶段。有稍微愉悦点的东西,让“这个人”更丰富一点。
栾:饱满一点。
林:你画画是不是先把一个基本颜色调出来,然后再画上去?
栾:不是的。我是一笔一笔的调出来慢慢画上去的。连底做得都不一样。要画很多遍,就需要画得那么厚。
林:你很讲究亮色和暗色之间的差别。形体的转折也很讲究。
栾:是这样。
林:从2000年看你的作品到现在,变化真的很大。
栾: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些自嘲,很好玩,他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说“成长”是否恰当还是一个问题。
林:还是想问,你为什么会画忧伤的题材?
栾:像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市场也好,怎么红也好,在情感上是一种悲剧。洗刷不掉80年代给我们留下的烙印,真的是这样子,只是大家都不敢表露出来。看起来都有种玩世不恭的感觉,很表面化。出来的时候都是穿得像模像样的,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我比较直。
林:从个人的真实情感和体验出发。这样的作品更容易打动人,你说的是人们心里边的那个硬伤。要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这个很难的。你早期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栾:我早期的画已经找不到了。奇怪了,一直在想念那些画。
林:你是昆明人?从小在昆明长大?
栾:我在四川出生,从六岁就到昆明来了,66年。
林: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
栾:正常的学画画?说不清楚。
林:你上中学的时候有美术兴趣班吗?
栾:中学的时候有的,但是我是在窗子外面。很眼馋的看别人在画。
林:上中学的时候才开始画画?
栾:不是,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那时候,画画总是一个人,找不到同类。班上有个同学就是喜欢画画,一看他画得好,感觉比你画得好。过了以后,就没有画画了。到了中学,我们班又来了一个画画的人。我又和他比的画,中学有一个兴趣班,里面有个人画得很好,叫付志刚的一个人。
林:这个人消失了吗?
栾:消失了,画得太好了。
林:你是哪一个中学?
栾:24中。
林:那就是云艺(老云艺)旁边这个学校了。
栾:对,就是这个学校。
林:那你天天经过云艺的大门。
栾:那会还没有。六几年还没有,当时是个工厂。云艺是79年恢复到这边的。
林:那年轻时候一起玩,现在还画画的朋友有吗?
栾:没有,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养成了我一个人画画的习惯。
林:一直以来都一个人吗?
栾:对,一个人。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在阳台上画画,很奇怪。
林: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你没考上?
栾:第一年,基本都没去。刚刚高中毕业,就下乡去了。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保留了一张我的景物,赭石色的一张。是我上高中时画的一张,非常好,是自学的。以前我的优点就是,画静物画的特别好。那个时候不断的练,就是和这些有关系,不能离开那段时期。人的发展,现在年龄大了回过头来看,是割舍不掉的。跟年轻时候有联系,以前说不清,现在完全说得清楚了。
林:你第一次参加展览是什么时候?
栾:没有,从来没参加过。当时对展览这个概念很陌生。
林:那会也有不少的展览,你去看吗?
栾:当时不懂,也没听说过什么展览的事情,更不要说进入市场这一类的。完全是天书。
是因为那时昆明有个艺术节。我去参加了(我原先画画不是像现在这种形式的画),画得很好看,技巧也很高。第一次参加云南省的展览。
林:是哪一年?
栾:86年或者87年,省里面的一个展览。还有一个是第七届全国美展,我参加了。
林:第七届美展是哪一年?
栾:89年,我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展览。我是最后一个递交作品的人。因为当时房子很小,光线也不够亮。我老是觉得画得不够亮,不断加白色,然后拿到阳光下看是泛白的。没有颜色,然后就开始不断的修改。我用三轮车把画拉到云南省美术馆,现在的那个地方(青年路)。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是最后一位送画的。我低着头进入美术馆,姚钟华看到我,就问我说这个画是你画的吗?我把画才放进去以后,就在想3天以后,退回来,我要把画摆到哪里去。我住的地方只有12个平方。
林:那怎么办?
栾:只有床底下可以放。就是在考虑,画拿回来以后该放在哪里了。怎么在去美术馆的路上就听见有人说,有一个人画得太好了。画写小人,我一听就是说我的。
林:因为画了很多人?
栾:画了很多少数民族,但是已经不像少数民族了。非常北欧,很神秘。
林:这些都是你青春期的辉煌历史,回忆起来应该还是很愉快吧。其实做艺术挺残忍的,一切靠作品说话,谁的作品更有力量,艺术家也许相互都在较劲。
栾:是的,很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