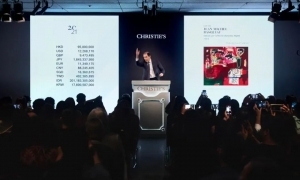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经历(打赢)了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这两场帝国主义战争之后,终于跻身西方列强之列。受到西方刮目相看的日本,随着其经济及武力的强盛,其版图扩张之心蠢蠢欲动,开始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放眼本国四周的茫茫大海,岛国日本把眼光投向其西边的亚洲大陆并且有意在此扩张势力,甚至想要仿效当时其他西方殖民主义者建成一个东方殖民帝国。这个大帝国梦想应是缺少战略纵深空间的日本的终极梦想。在它得手中国台湾、吞并朝鲜之后,进而觊觎中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开阔的战略空间,图谋将其纳入帝国版图的计划,成为了日本处心积虑想要早日实现的“国策”要务。
进入20世纪,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策划了柳条湖事件。以柳条湖事件为起点,日本关东军展开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行动,于是在日本则有了“满洲事变”之说。1932年3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扶植起傀儡国家伪“满洲国”,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对于中国东北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
随着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逐渐扩大与深入,有相当一批日本人出于各种目的来到中国从事摄影活动。在他们当中,既有以其他职业身份到伪“满洲国”工作,但在谋生的同时仍然以摄影爱好者身份从事摄影创作的人,也有作为各类新闻媒体的记者被派遣到中国战场与各地进行摄影报道的人。此外,还有在来中国观光的同时也进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而受宣传伪“满洲国”的任务驱使,来到中国各地拍摄用于“国策宣传”照片的专业摄影家,则可能与以上三类人都有不同。因为他们是担负“宣传”任务的摄影家,因此其工作性质与报道摄影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这些担负“宣传”任务的日本人,在中国通过他们的照相机取景器看到了什么?他们通过他们的摄影想要“创造”出什么样的异国现实?他们的照片反映出了什么样的中国观?他们如何以摄影为“国策宣传”服务?这一系列问题或许可以从他们现今留下的某些视觉文本窥知一二。
在这些视觉本文中,被称为日本现代摄影巨匠的木村伊兵卫(1901-1974)留存后世的摄影集《王道乐土》可能颇具文本价值。本书编辑(当时日语用语是“编装”,有编辑装帧之意)是后来被誉为日本现代平面设计大师的原弘,于1943年由ARS出版社在东京出版发行,印数1500部,硬面精装,纸盒封套。
木村是于1940年5月到6月间,应“满铁”总局之邀,对当时的伪“满洲国”进行了为期40天的访问。日俄战争后,日本接受了原来由沙皇俄国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将其改称为南满铁路。1906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成立并于1907年把会社总部迁至大连。该会社简称“满铁”(Mantetsu)。从开始只在中国东北经营铁路业务到逐渐扩大其经营范围至几乎国民经济所有领域,“满铁”成为了以公司名义实行殖民地侵略的“国策会社”。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SouthManchuriaRailwayCo.),是由日本政府直接管理的推行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庞大机构,也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实,早在1936年,木村就曾经应“满铁”之邀,与摄影家中山岩太一起访问过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他于1937年还来到上海与南京,跟随日军行动,展开摄影活动。而在出版本书《王道乐土》之前,其实木村已经在战时日本的对外视觉宣传中出力颇多。日本因为侵略中国而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孤立境况,图像宣传于是成为了当时的日本打开困局的努力之一。木村本人就在东京举办过《展现日本摄影展》(1937年)和《南京-上海报道摄影展》(1938年)等个展,也出版了《透过莱卡所见到的日本》(1938年)与《日本的姑娘》(1939年)等摄影集。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宣传性质的画报(《前线》、《日本旅行》及《摄影周报》等),都有他提供的大量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渡满”于他应该也属顺理成章之行。
在《王道乐土》这本画册里,我们会发现,相比出现在多个单元里的俄罗斯人(非“东洋人”)的存在,日本人的存在并不突出。这也似乎显现了面向西方、以西方价值观为取向而走向现代化的日本的宿命,那就是既拼命想要成为亚洲人的西化模范,但仍然在形象生产上艳羡有着非东洋人形象的俄罗斯人而展开大量拍摄并展现(炫耀)之。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俄罗斯人形象只是服务于“民族协和”的形象道具。
木村伊兵卫作为一个“抓拍圣手”,其摄影具有平实中饱含隽永的风格,画面一般不取极端视角,人与景物之间的关系恰到好处。画面不以嚣张的动感吸引人。画面既有报道摄影所需的信息,也足够把握到人物的气息与性格,因此照片都颇耐看。他的风格在拍摄本书时已经基本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观看诱导,因此从宣传的角度看,不以让人心生紧张甚至反感的视角而取平实视角应属更为成熟老练的手法。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本书编辑照片的功夫,而正如版权页所显示的,这是由平面设计师原弘所实施的照片编辑。当一群照片被以某种方式加以编辑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照片拍得有多好其实已经意义不大。如果照片有足够的视觉信息,并且能够被善加编辑,那么事情实际上就转变为如何使用照片的问题了。一群照片被以某种方式组织与排列起来,其最终的意义生成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人们如何编辑这些照片。试看此书中的一些照片的编排,我们就会发现多是经过费心斟酌的。这些照片,或强调伪“满洲国”与日本的异质性,或突出伪“满洲国”现代化建设的气势。当然,也突出这块“新土地”对于日本与日本人的意义。比如,在“镜泊湖”单元,书中照片着力呈现日本人开拓团的生活。此单元开首有段文字:“来此地的目的并非为了拍摄美丽的风景照片,而是为了访问在对岸的最初的开拓团镜泊学园。以许多牺牲为基础,年轻的开拓者们以一种快乐家园式的学园终于开始走向完成的喜悦,充满了自信地工作着。”在这样的文字基调之下,木村以五张照片呈现了日本人开拓团的充满了活力与幸福感的形象。在第一个对页中,在左边画面,他以仰视的角度展现了四个青年男女。他们都以欢快的笑脸向前展望,画面的影调很是明快。而右边画面则取俯视角度,呈现了团员在湖边待渡的情景。这也是具有象征性的画面,因为启航所给出的想象空间,与“开拓”殖民地的意志正好合拍。而画面中的近景人物也是笑意盈盈地抬头望着他的镜头。在第二个对页中,左边画面中给出了一个年轻甚至有些童稚气的开拓团员的肖像特写。他的眼神中有高光洋溢,显示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而右边的照片则是无垠的田野,画面中两个开拓团员一前一后背朝读者向着画面纵深走去。这样的空间处理,显然应和了、也印证了疆界逼仄的日本帝国对于空间的渴望与领土扩张的想象和欲望。这也同时唤起了读者对于“新土地”所具有的丰饶物产与生产的联想,并且给出一种有关伪“满洲国”前景的前瞻性期待。而本单元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个跨页,标题是“水田”,画面以蓝天白云远山为背景,呈现团员在被分割成几何形的水稻田中耕作的情景。以这样的远眺式的画面处理,木村非但将辛勤的劳作诗意化,并且以这样的排除了具体细节的开阔画面,实现了以诗意的情景讴歌“新土地”上的劳动者(也是殖民者)的目的。从编辑手法来说,这样的照片处理,充分反映了编辑者具有如何在有限空间里以并置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开拓出照片的意义的能力。如果说照片中的开拓团员是在以体力开垦殖民地的物质空间的话,那么如木村这样的帝国知识分子,则是以他们的智力为团员们的开垦行为开拓出了意义(也是精神)的空间。
在摄影集的最后一个单元“新京”里,编者用了两个版面(也是摄影集最后两个版面)表现了新京机场。这么做显然隐藏着期许伪“满洲国”的现代化大展鹏程之意。然而,所有这一切看似“民族协和”、“安居乐业”的欢快情景,都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的帝国观看者对于异国人民的视觉观察、呈现、安排与定义。处于君临一切状态的帝国摄影者木村,同时也是选择者与归类者。他只能根据帝国的逻辑来选择他认为好的(也是符合帝国审查要求的)景象入镜。因此,他的镜头不会收入令人难堪的画面,也因此,这是一本只是宣传而不是报道的摄影集。在此书出版的1943年,日本已经进入到了战争难以为继的地步,包括摄影材料在内的各种资材供给开始发生困难,但此书仍然用料豪华,可以推想是因为它具有某种使命才会在此困难时期获得出版“准生证”。然而,即使木村已经恪守了对于报道的严苛要求,但此书出版后据说还是触犯了军方而被禁止发行。
身处战时的帝国摄影家木村的复杂性还在于,他早在日本还没有陷入战争之时,就已经以一个民间人士的身份积极地介入到了国家的宣传活动中去了。从木村效力(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国家的行动,我们回头来看,大时代下的文化人,究竟如何自处才能做到不为虎作伥?文化人如何能够摆脱为政治利用的宿命?事后能不能以我只是“职人”(匠人)为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人”(匠人),摄影家只要把“活”做好,不管这“活”的性质如何是否就可以逃避谴责了?
木村伊兵卫(1901-1974)出生于东京下谷的富裕之家。1919年京华商业学校毕业后,于1920年赴台湾台南市的砂糖批发店“安部幸商店”任职。在台期间,他经常出入台南的远藤照相馆,学会了摄影。1922年,他回到日本,并于1924年在家里的帮助下开设了营业照相馆谋生。但在1925年,他的照相馆被大火烧毁。他于1930年购买了当时刚面世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开始以街头抓拍的手法拍摄市民生活。他的作品在当时提倡现代主义摄影的杂志《光画》上发表,以其现实主义的手法奠定了报道摄影家的先驱地位。他一生唯莱卡小型照相机是用,被尊为抓拍圣手,享誉日本摄影界。1933年,与日本国家对外宣传有密切关系的留德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创办摄影图片社“日本工房”,木村与平面设计师原弘、电影演员冈田桑三等人一起参加。1934年,他脱离“日本工房”,与原弘等人另组“中央工房”,并设立属于“中央工房”的国际报道摄影协会。此协会专事向海外配发日本对外宣传照片,性质上属国际性的图片经纪社,由木村任会长。
战后,木村于1950年成为日本摄影家协会第一任会长。木村一生曾经七次访问中国。1971年,在中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后,他被中国政府邀请出席当年的国庆节庆典。1973年,他带领日中友好摄影家代表团访华。此团队中有林忠彦、蓧山纪信、北井一夫等人,均为日本摄影的一时俊彦。据1973年与木村同行的日本摄影家后来告诉我,当时林忠彦总有一种惴惴不安,因为他深度介入过军方主导的在北京的摄影活动。而木村则老僧入定,绝口不提战时的中国之行,埋头拍摄新中国给他安排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