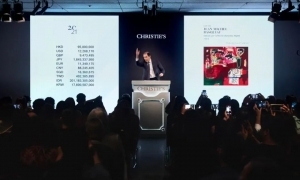周思聪的《矿工图》
读周思聪的《矿工图》,如瞻仰丰碑。
《矿工图》,作为周思聪绘画艺术的代表作,体现的是其巅峰状态的艺术风貌。《矿工图》,是一座中国当代人物美术史上的里程碑,是一座中国近代抗战史的浓缩殿堂。它把中国人民最为屈辱的艰难困苦,用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定格于斯,凝聚在焦墨与宣纸之间。作品既承前于恩师蒋兆和、画友丸木的国家与民族主题,又突破了七八十年代“高、大、全”的主题性表现手法。以几何线条的参差交汇,人物与意象的叠加错落,抽象与变形的夸张曲折,重新解构了绘画语言,选择了全新模式,构架了发人深省,撼人心魄的民族呼声—《矿工图》。
《矿工图》的创作
“我爱平凡的人”,是周思聪终身的艺术语言。萦绕周思聪一生的,是她对劳动人民苦难的理解,对历史的反思,对艺术的追求。早在1966年,周思聪与卢沉夫妇就萌发了创作《矿工图》的设想。周思聪出生于1939年,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年头,日军侵略下华北沦陷区的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百姓深受日军荼毒。这张一家四口的合影,大致拍摄于1943年前后。黑白的影像中,是一家人朴素的衣着与神情。周思聪像男孩子一样剃着光头,与哥哥唯一相区别是中式单褂上多了一枚装饰胸针。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使得幼年的她好强而羞怯,少言而多思。日军侵略下底层民众的乡镇生活、草根情结与忧患意识,从小养成并影响了周思聪一生。
周思聪接受了良好的美术教育。少年时代就读美院附中,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先生、叶浅予先生、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以及其它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美院附中就读时期,周思聪就曾多次观摩蒋兆和先生代表作《流民图》长卷,她在《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怀念蒋兆和先生》一文中回忆道“少年时,我第一次见到蒋兆和先生的宏图巨作《流民图》,当时幼稚的心灵曾为之颤抖,从此便不能忘怀。以后每观此图,总禁不住心头的激动。是先生的画,引着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理解人生。”
1956年,日本反战画家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的《原爆图》(描绘广岛原子弹爆炸场景)在中国展出。“那时,我还在中学读书,这幅作品使我感受到巨大的冲动,画面上那些受难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周思聪:《陪同丸木夫妇旅行写生记》)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夫妇的《原爆图》这些以重大社会灾难为创作主题的厚重作品,强烈冲击着周思聪少年时的心灵,深刻影响了她以后的创作方向。长久以来,周思聪与卢沉一直有一个共同的夙愿—了解矿工,塑造矿工形象,以矿工来代表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为了《矿工图》的创作,他们先后去过几座矿山,熟悉矿工的气质、性格,了解他们的苦难、斗争和喜怒哀乐。《矿工图》计划以矿工史为主线,以组画的形式完成。农民背井离乡,逃荒求生;到煤矿挖煤,走入地狱之门;与厂主、监工、饥饿、瓦斯搏斗,人间炼狱般的生活;直至斗争胜利,当家作主,展现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整个历程。但由于最初的思考不甚成熟,还停留在一般的说明层面,加之文革的十年浩劫,正式的创作过程,在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开始。
为此,1980年4月,周思聪与卢沉共赴吉林辽源煤矿,深入矿工生活。“之所以选择这个矿,是因为它曾经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地方。这里的老矿工能活到今天 ,可说是奇迹了。他们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的人。”(周思聪《历史的启示》)他们住在矿区,每天步行十几里山路体验井下作业。他们发奋工作,画了大量的速写,查阅日伪时期的史料,搜集口述历史。一百多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之后,一张张草图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他们产生了以民族斗争为主线的全新构思,意图通过表现中国人民苦难的历程,激发人们不做奴隶不信神,直起脊梁做主人的民族斗志。同年6月,周思聪恰好有机会到日本参观访问,这使她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可以拜访她十分敬佩的日本著名画家丸木夫妇。在丸木夫妇的展室中,周思聪欣赏了大量的习作和几件巨幅创作,除了著名的《原爆图》外,还有一件巨幅作品—《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屠杀场面,使周思聪难以抑制情绪的激动,泪水夺眶而出。这次难忘的拜访,不仅给周思聪启迪,更加坚定了她创作《矿工图》的信念。“一个外国人,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谴责本国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当然更应该表现实际上发生和存在过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灾难,以及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以激励人们使这种人间惨剧永不再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切切实实的努力。”
回国后,她与卢沉立即着手《矿工图》组画的创作。他们一反过去常用的构图方法,尝试探寻在同一画面中,表现不同时间、空间的物象,交错、并置、割裂、变形用错综复杂的幻影表达悲惨的场景。其目的不是使人赏心悦目,而是令人为之震撼进而深思。1980年完成《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1981年1月创作《矿工图》之六《遗孤》,1982年3月创作《矿工图》之二《王道乐土》,以及之三《人间地狱》。艺术形式的探求,永远要服从于对内容更深刻、更有力的表达。为了表现压抑到窒息的状态,他以浓重的黑色主调、变异的形体、悲苦麻木的神情,描绘人物形象,以割裂、拼贴、组合,表现积压的时空。站在画前,令人感到阴冷、压抑、痛苦和震撼。我们能从画面中读到的,是曾经的历史灾难和民族的存亡危机,并由此引发人们对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思考。令人遗憾的是,周思聪没有能按照最初的设想,完成九幅作品的全部创作。由于沉重的创作题材,带来情感上的巨大起伏等综合性因素,使她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只完成了《矿工图》组画中的《王道乐土》、《人间地狱》、《同胞、汉奸和狗》、《遗孤》四幅作品,成为“未完”的浩浩悲歌。其中《同胞、汉奸和狗》,现藏北京画院。
在八十年代初期,由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已经没有人再公开说《矿工图》“污蔑工人阶级形象”。而作为一种崭新创作形式的探索,仍然面临诸多争议。1981年,周思聪在至好友马文蔚的信件中曾有这样的记叙:“昨天下午,画院破例为我的习作开了一次座谈,连一些油画组的同事都参加了。我没想到,这是历次习作观摩反映最强烈的。会上有争论,多数同志支持我的探索,为我不维护过去,踏出新的足迹而高兴;也有些同志惋惜,说我脱离了群众的审美观。两位领导也参加了争论。本来说开一个半小时,结果开了三个多小时。从我的习作说起,又引出了艺术的民主,美与丑的标准,艺术领导和领导艺术等问题,谈得很自然。我将更坚定的走下去,也许三年之内我不拿出什么作品问世,也许三年之后又有什么“形势的变化”,使我该拿出的作品不能拿出来,这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大家期望我成功。”艺术语言之外,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大型题材,还要面对来自政治环境的压力。1981年由于中日关系友好的缘故,《矿工图》被指责为不识时务的创作。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日本发生了有意隐瞒和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事件,《人民日报》等媒体又要刊登《矿工图》组画中的《王道乐土》。重重波折之后,1984年,周思聪第二次访日时,终于如愿带去了《王道乐土》和其它作品共计三十多幅,在东京上野美术馆隆重展出,轰动日本。日本《每日新闻》于1982年7月14日晚刊刊登了《王道乐土》并在通讯的结尾做出如下评述:
“毕加索画了一幅《格尔尼卡》,声讨纳粹的狂轰滥炸。丸木夫妇画了描绘原子弹轰炸悲剧的《原爆图》。《矿工图》则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无论哪一幅画,都怀着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对和平的祈愿。”《矿工图—王道乐土》变体稿 《矿工图—王道乐土》变体稿,与后来的最终稿相比较,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分析,很可能是一幅迫于政治需要而未能公开发表的重要作品。
将变体稿与最终稿比对,我们可以看到:两幅画有着共同的基因,宛如一对孪生姐妹。变体稿尺寸178×240cm,最终稿尺寸177×236cm,几近相同。在人物刻画上,两幅画面中卖子医夫的母亲、沿街卖唱的愁苦父女、怀抱啜乳婴儿的老母、神情麻木的老人、紧握刺刀的日本士兵男女老少的悲苦形象、绝望与号泣如出一辙。而在画面构成上,变形、交错、并置、割裂,悲惨的场景、压抑窒息的氛围同时逼人而来。但是这两幅画面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变体稿的画面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事件。东条英机与汉奸头子觥筹交错,其背后日本士兵发号施令,汉奸惟命是从。在日军雪亮的刺刀驱赶之下,大批的中国劳工进入满洲签署卖身契。而同时,满洲城乡四处飘扬着日本国旗,撒布着日军的宣传标语“欢迎华北劳工入满洲”,貌似一片欣欣向荣。而在画面的底部,也是社会的最底层,老弱病残孤苦无依,饥饿伤痛流离失所。一面巨大的日本国旗,隐约覆盖在整幅画面的中上部,其中心投射在举杯相庆的东条英机身上。把侵略的伪善与残酷,揭露并鞭笞的极为彻底。在公开的最终稿中,东条英机消失了,汉奸消失了,日本政府粉饰的虚假繁荣和宣传标语也消失了。除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只有一面日本国旗和一名日本士兵出现在画面的边缘。画面的主题也随之转移,由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揭露和对中国人民奴役的谴责,转向了对人民无尽苦难的描绘与同情。纵观变体稿与最终稿的不变与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作品的不变,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其创作手法、艺术语言已经达到了周思聪的预期,不需要再做进一步调整。作品的改变,是创作主题的转移。由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转向对劳苦人民的同情。
从终稿款识可知,《王道乐土》最终稿完成于1982年3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1982年春季美术展览会,时值中日建交十周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时间点,两国友谊之花盛开,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感情,日益友好起来,谴责日本对华侵略的呼声也渐渐消失。《王道乐土》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控诉,与当时国际政治的需求不相符合。特别是在变体稿中,对日本侵略的直接描绘,揭露所谓“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并不是日军所宣传的“共存共荣”的自由幸福乐土,而是谎言与刺刀、侵略与欺压、痛苦与死亡的人间地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品,有碍于中日友好。
然而,历史的演变总是富于戏剧性。1982年3月,经过修正的《王道乐土》正式公开发表。时隔不久,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史实,引发了中日之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件曾被认为调子太低沉艺术作品,此时得到的关注反而多了起来。这在周思聪的记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教科书事件发生了。关心《矿工图》的人忽然多了起来,人民日报来人说,要刊登《王道乐土》,并要同时刊登丸木夫妇的《南京大屠杀》。当时不乏人指责我不识时务,这种画似有损于中日友好,现在又‘赶上点儿了’。
我不由得有一种受人愚弄之感。倒好像我在赶时髦。难道艺术就该服从这种摆布吗?艺术作品非要在政治需要时才被肯定吗?如果没有去年的事,我的画今年能起到伸张正义的一点作用,也是令人欣慰的。其实,认真想想,日本人的狂态与我们有些人的献媚不无关系。讨好别人定会被别人小看。中国人用血写得历史,都不敢理直气壮,未免太软骨了。”(周思聪致马文蔚信1982.8.4)信中提到的‘去年的事’是什么?在《王道乐土》的创作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周思聪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伸张正义’?在公开文献中已无从查考。但从《王道乐土》终稿的完成时间1982年3月来看,1981年至1982年初《王道乐土》的创作并不顺利,发生了很多波折,而导致周思聪最终淡化了反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的创作主题,转向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与呼号。
历史总是会被时间还原以真相,即使真相曾因为各种原因被掩饰。而还原的初衷是使悲剧不再重演以及对和平的祈愿。 不得不提的是《王道乐土》变体稿中画面的空白部分。这片空白,恰恰处于整幅画面的黄金分割位置,上下贯穿隐现的日本国旗,并将其分为两半。在整张满密压抑的画面中,极具震撼力度。这块空白如何产生?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谜。可能是意外所致,也可能是局部败笔舍弃重画,也可能,像周思聪《广岛风景》(1986年)中的撕毁一样,是突破性创作的一个部分,以表达不可修复、不可逆转、不可遗忘的沉痛创伤。而无论出于哪种原因,这块空白以当今的艺术眼光来看,是整幅画面中,最值得喝彩的创造。艺术的魅力也许与历史的偶然一样,正在于此。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