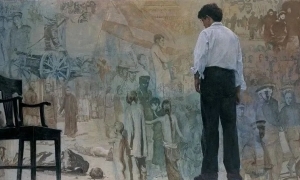2025年3月8日至4月7日,成都画院举办罗敏&邢丹文双个展。展览以“故园”与“别处”为题,在两位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光谱中,照见当代社会里个体生命的根系纵深与精神迁徙。
罗敏和邢丹文两位艺术家以迥异的艺术语言,构建起“向内生长”与“向外观照”的镜像对话。罗敏的“故园”叙事如同隐秘的年轮,在生活的褶皱里提炼永恒诗性;邢丹文则以“别处”为棱镜,于时代症候中叩问存在本质。她们的作品在成都画院这座古老的院落空间中,在私密与公共的张力场域中,缓缓铺开多维的精神图景。

艺术家罗敏(左)与邢丹文(右)在布展现场
罗敏:绘画中的人生迁徙与故园记忆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罗敏个展“故园”展出了《鸟语花香》、《敏和莉》、《春游》等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罗敏将四川童年记忆作为叙事核心,以离乡者的距离感与时间沉淀后的清醒目光,重新梳理个体与故土之间微妙的情感关联,而并非是简单地复刻乡愁。正如她所言,地域性的明晰往往源于“走远”后的回望,而这种回望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更是精神层面对记忆碎片的打捞与重组。
她作品中拼贴的时空、跳脱的色彩肌理,恰似被现代生活割裂的时间长河中浮沉的记忆孤岛,画面中若隐若现的痛感似乎揭示着记忆、情感与人生的复杂性。两条粗黑的辫子是对母亲的影射,飘零的树叶是时间的残片……这些源于私人经验的隐喻图式,虽然是带有体温的个人历史档案,但同时也映照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精神漂泊的群体性回响。
在过去一年中,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各地,罗敏在旅途中用绘画完成了一篇篇的“日记”,那些他乡“日记”与这些承载着故园记忆的作品相互渗透,让地域文化不再是封闭的符号,而转化为开放共生的精神容器。

艺术家 罗敏
Q:
展览展出了你的许多与四川童年记忆相关的作品,为什么选择在成都画院这个空间呈现它们?地域文化如何影响创作叙事?
罗敏:
多年前参加过成都画院的一个群体展览,所以对这个场馆有很深的印象。到北京工作后作为访客来过几次成都画院,每次都有“回来”的感觉,我想是因为这个场地有很强的四川在地的味道,所以能勾起稀疏的回忆。这部分作品的“地域”性是“走远”后在心里变得明晰起来,然后开始创作的,我想可能也跟年龄的增长有关。
Q:
你的作品以拼贴重组时间和空间为特点,色彩运用也极具个人风格。这种视觉语言是如何形成的?背后是否有对记忆碎片化或流动性的思考?
罗敏:
时间在不停被各种事情挤压和不同城市的迁途中打断之后,经历着的事情往往会变得特别模糊,能想起来的都是非常个体的、遥远的事情,由小到大的个人经历被自动地切割了,像碎纸机一样,但时常清晰地跳脱出来。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Q:
这些带有童年记忆的作品,似乎并不是完全的轻松、欢愉,而是带有一些隐隐的痛感,对此你怎么看?
罗敏:
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况且有些东西你经历过就不会忘记。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Q:
你提到展览不仅是作品陈列,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在创作这些承载个人成长记忆的作品时,如何平衡私人经验与时代大环境造就的群体情感经验之间的关系和表达?
罗敏:
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分离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命运和背景。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从事架上绘画的人,没有必要一定要想怎么去画画才算是跟得上潮流,既不需要去向成功的50后们看齐,也不需要跟热闹的80、90后接轨,跟着自己的内心和“品味”走,跟着自己的人生经历走,成为某一个特定时期和人群的诉说者,或者成为只诉说自己的人,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足够真诚就好。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Q:
策展人提到你和邢丹文都曾在全球多地生活,但作品中依然存在对“故园”的回望。你如何将异乡的“别处”经验与四川本土记忆融合在艺术创作中?
罗敏:
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都是想通过某种或者多种方式传达一种自己认同的精神世界,所以无论故地还是他乡,都会传达出特定气质的作品面貌。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Q:
在你看来,邢丹文的作品与你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内在链接?她的作品是否也给你带来了某些触动或者思考?
罗敏:
丹文和我的作品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手段和媒介,但我看她的作品中有和我一样的孤独和爱的存在,无论是“故园”还是“别处”,关注的都是人的心理和情感,都是游离于某种孤寂情绪之中的人性表达。她作品中的强度是非常有能量的,也是我特别喜欢和欣赏的那一部分。


“罗敏:故园”展现现场
邢丹文:时空切片中的错位漫游

艺术家 邢丹文
艺术家的使命不是给出答案,而是保持对世界的持续发问。邢丹文的作品,在现实与记忆、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世界的交界处,以模糊且错位的影像语言,用定格的“此刻”,打捞起现实的碎片,丈量与追问存在的维度。
此次展出的作品《别处》、《纽约》宽幅、《长卷》A和B、《梦游》在邢丹文的艺术生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是她摄影艺术和持续三十余年的精神漫游的开端,更是她用摄影切开现实表皮,将自我链接到更广泛的文化历史空间的通道。
从1989年最初按下快门的直觉性纪实摄影,到纽约留学时期对宽荧幕美学的颠覆性实验,再到《长卷》系列与中国传统美学的相遇,她在主动打破摄影艺术的固有范式同时,也在不经意间触碰东西方艺术传统的深层共振。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Q:
此次展览展出了许多早期的黑白影像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是首次公开。为何选择在成都画院这一历史空间中呈现它们?
邢丹文:
这次展出的作品多数是我艺术生涯起点阶段创作的,最早的一件距今有35年了,其实当你了解这四件作品后,你会发现,它们一环接一环,是紧密关联的。当时我初遇摄影即陷入热爱,在陌生与未知中开启了对这一媒介的探索历程。我是绘画专业出身,那时虽没有受过摄影专业训练,却可以从绘画者的空间观察力介入摄影,保留了对影像最本真的感知,所以我早期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直觉性和纪实特质。
在这一阶段之后,我的创作转型为更有计划性的观念摄影,但我一直在思考早期那种感性且直接的拍摄方法究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拍?又为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什么?所以,多年来,我也会持续回看这些作品,既是对创作本源的追溯,也是自我认知的深化。我觉得,它们不仅承载着我艺术道路的起点印记,更在不断重读中给予我新的启示,这也是我始终珍视并选择在这次展览中呈现这些早期创作的主要原因。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Q:
展览主题“别处”与“故园”在气质和主题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呼应?
邢丹文:
我的摄影创作始于1989年,真正形成脉络是在1999年到纽约之后,那些游走于街头巷尾的黑白影像构成了《别处》这个系列。包括后来我在行走过程中,透过时间和空间抓拍到的影像,这些看似零散的,但又是大量的瞬间碎片聚集在一起时,让我看到了一条线索,也是贯穿这次展览题目“别处”的线索。“别处”于我而言,既是地理坐标的位移,更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状态。常有人误认我久居海外,我自己也常因故土与异乡的双重疏离而产生一种错位感。
当我被邀请参加这个展览时,我刚好在成都,就去看了展览空间,当踏入展厅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在我16岁第一次探亲的那个夏天,曾被家人送来这里,因为七孃朱佩君是家族里唯一的艺术从业者,在她的安排下度过那个暑假,记得我第一张油画就是在何多苓老师的画室里体验的。虽然我祖籍成都,但40年间鲜少来过。多年来的行走经历,让我常保持客居者的观察视角,这种游离状态,在成都画院展览空间里好像获得了宿命般的呼应。

邢丹文与朱佩君院长雕像一起
Q:
这种“故园”或者“故乡”情结如何在你的艺术实践中与全球行走的经历和感受共存?你如何看待个人在地经验对作品深层结构的塑造?
邢丹文:
1998年到2002年间,因为ACC的学者奖金和SVA的院长奖学金,我在纽约渡过了一段人生很重要的时期。当时对宽画幅影像的审美语言特别感兴趣,一是审美风格非常独特,二是有强烈的诗意化表达。虽然我当时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功课、看了一些优秀作品,但我的想法不是一种简单的格式和审美,而是观看的方式和大脑如何鉴别记忆中的空间的方式,于是我是在一种流动的拍摄中重建出虚构的宽画幅影像和意念空间,这种反单幅抓拍的拍摄非常实验和即兴,充满了意外中的失败和因错误带来的惊喜,也因此造就了《纽约》宽幅系列的独特语言。
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和北京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因为我人生成长最关键的年段是从北京开始的,并目睹了北京城自八十年代末至今的变化。所以在纽约时,我对北京有着很强烈的怀乡情节。1999年暑假期间,当我带着这套新语言回到北京,想要按照《纽约》宽幅系列的方式,以旁观者的眼光,重新观看北京、拍摄北京。
当时,我在后海胡同里连续拍摄的胶卷在冲洗时又遇到了新的“意外”:按照三、四格一拍的方式拍摄,但冲洗时发现因为画面贯通流畅的完整性,使我根本无法按预设进行剪切。正是这个“意外”,催生了《长卷》A和B。
这两组在120毫米的胶卷上连续拍摄的关于北京的图像,是胶片由相机直接拍摄,没有经过任何电脑合成或数字化效果。《长卷A》聚焦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人类活动;《长卷B》捕捉了北京老街道和建筑,通过抽象的图像,我把北京的传统建筑也进行了拆解,其实也是在隐喻城市化建设中,对老建筑进行破坏式拆除的伤感和反思。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邢丹文,《纽约》系列, 1999
Q:
传统东方式的观看和表达方式,与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创作方法,哪个对你影响更大一些?
邢丹文:
当代艺术的观察和表达方法影响更大一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很不同于当下,在我们的出生年代,首先要破四旧,所以直到成熟后才意识到传统的价值和精髓。从文学到艺术,我们小时接受的大多是西方式教育,更确切地说是俄国体系。我是到了30多岁,才开始真正发现、理解和品味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
201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Ink Art水墨”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选中了我的作品《都市演绎》和《长卷》。我被邀请参加与策展人对话的论坛,那时我才知道,策展人何慕文(Maxwell K Hearn)为什么要选我的作品。他觉得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在于一种景观式的观看方法,而我的作品呈现的正是散点透视的景观图像。
他当时问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长卷》是不是按照传统中国长轴绘画的风格去拍摄的?”我说:“不是。我是以反摄影的实验探索为出发点进行的创作,在我完成制作后,才发现传统‘长卷’竟在其中。”在这几件同期作品中,我一直想打破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的单画幅拍摄方式,并在实验性的运动中连续拍摄、重建虚构景观和空间,完成之后发现竟与中国传统长卷绘画的观看方式一致。这个创作经历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所走的路径有时候就是圆的,起点和终点终会在一处相遇。



邢丹文,《长卷》系列,1999-2000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Q:
你的作品中,尤其是《梦游》这件作品,在虚与实之间呈现强烈的“梦游般的错位感”,为什么会对这种美学形式着迷?这种视觉语言是否承载了你对记忆、流动或疏离的思考?
邢丹文:
《梦游》是我SVA的毕业创作,创作期间就被南条史生发现,完成之后直接被选入横滨三年展。这是我第一个参加国际当代艺术展览的作品,也是我的第一件Video和第一件装置作品。
千禧年前后,纽约城和北京有很多相似之处,拥有国际超级大都市的繁华景观,也有城市边缘混乱老旧的灰暗地带。当时在纽约时,我竟然经常感觉并没有离开北京。这种怀疑性的观察和体验时常会进入我当下的存在状态,对我的创作观念影响是比较大的。实际上,这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我去巴黎的经历。因为从小学习绘画,在当时我的想象中,巴黎是艺术的殿堂,是辉煌的、美好的、绚烂的。但当我坐朋友的私车,从德国穿过几道边境在凌晨到达巴黎的时候,这座我理想中的城市给了我极大的落差,它是昏暗的、脏乱的、落魄的。“走失巴黎”带来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感,引发了我对很多事的思考和认识,尤其是现实存在和大脑记忆及想象之间的关系,错位所造成的“真假”困境。这在我后来的创作中常常乎隐乎现,游走其中。
《梦游》创作的起点是很直觉的,与时空错位的经历有关,期间在我做了很多心理学方面,包括对梦境的研究后,我更自觉地认识到了这种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特性。这件作品可以说是我在纽约生活、创作和学习整个阶段的一个特别充分的总结。

邢丹文,《梦游》,双视频装置, 2000-2001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Q:
具体来说,《梦游》是怎样突出这种错位感的?
邢丹文:
《梦游》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影像,另一半是声音。声音代表了“我从哪里来”即中国,影像代表的是“我在哪里”即国外。
静态的图像是黑白的,而且都是从“纽约”、“长卷”和“别处”中裁切出来的,只有动态Video的部分直接摄像,是彩色的但又做了负像处理。
在这件作品里,我借“错位”探讨到底是现实更真实,还是记忆和想象更具有真实性。从这以后,我发现历史很难是绝对的真实,因为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邢丹文,《梦游》,双视频装置, 2000-2001
“邢丹文:别处”展览现场
Q:
你怎样看待新的图像生成工具和审美对传统摄影的冲击?(比如AI)你会借助这些新工具进行创作吗?
邢丹文:
虽然我还没有实际使用过,但我对新科技和新工具的态度是开放的。至于审美,我认为,当被理论化、分类化和风格化的时候,就意味着“美”的死亡,这种矛盾在数字化时代愈发凸显。
数字技术对图像生产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推动力,但同时也埋藏着深层危机。
视觉创作的原创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消解。指令性生成的便利性让操作者沉溺于即时性实现感和生产,而真正需要生命体验沉淀的原创质量变得愈发稀缺,产品往往过眼云烟。在这个时代中,当市场被海量数字图像淹没时,真正具有原创价值的作品可能会遭遇冷漠。大众审美往往趋于平庸,多数从业者包括艺术家、藏家、画廊也更倾向于复制已验证的成功模式。我认为只有具备专业深度判断力的策展人和学者,才可能成为发掘原创艺术的伯乐,但这类策展人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中十分稀少。




邢丹文,《别处》系列, 1989-1999
Q:
在你看来,罗敏老师的作品与你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内在链接?她的作品是否也给你带来了某些触动或者思考?
邢丹文:
通过成都画院这个双个展,我和罗敏产生联结,这种缘分弥足珍贵。罗敏的作品聚焦于母女关系等细腻的私人记忆。这种向内探寻的创作路径与我形成了一种有趣对照。她是通过艺术不断梳理内在的生命经纬,而我是通过个体生命经验出发,借用外部世界的同时与自我产生互动,再将这种私人体验转化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的存在境遇。她更多的是向内找自己与生活、生命的关系,我更多的是向外找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是在“找自己”,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

邢丹文、策展人曹筝琪娜、罗敏
2024年12月第一次见面
成都画院
写在最后
此次展览,在空间上打破了传统白盒子式的布展格局,以沉浸式的情感渲染,打通了艺术作品与观众的精神通道。在成都画院这座始建于清代中后期的建筑中,两位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在时空的缝隙间构筑起崭新的文化维度。游走于展厅,古老与当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位女性艺术家在保持独立创作路径的同时,彼此的光斑在某个层面已悄然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