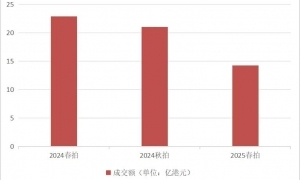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之一,《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究竟想表达什么?20年后,十名创作人,以及活动协调者,摄影,共十二人首度发声。
当代艺术究竟该如何欣赏?裸体在作品中是否真的有任何意义?这件作品想表达什么?这是年轻人的癫狂之作吗?为什么威尼斯双年展选中了这个作品?这十个当年的年轻“盲流”艺术家今天在做什么?步入中年的他们,在获得成功后如何再评价这个作品?
针对这件影响巨大的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始终存在种种疑问。而当年,创作者们迫于生计,在完成作品后即各自忙碌,始终没有回答上述问题。
20年后,《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创作者们首次集体发声,对这一作品做出解读,也让这一作品真正完整了。采访是在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分别针对十位联合创作者,活动协调者孔布,摄影师吕楠,共12名,单独进行的,我们几乎没有给创作者们留出任何准备时间。有意思的是,十二名集体创作者,做出了十二种解读。而这正是当代艺术倡导的精神,那就是:面对当代艺术,独立思考的精神比盲目点赞或反对都更重要。
采访由观鲤台联合著名策展人杜曦云共同完成,分六期发布,这期里的受访者是:朱冥vs段英梅
艺术家 | 朱冥
朱冥
为了心中的艺术之梦,他高中毕业就来到北京,这期间经历了十年的贫困和四个月的拘留,也曾迷茫和痛苦,但始终坚守对于艺术的信念,今天的朱冥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之梦,成为了著名艺术家,但依然在自我的艺术之路上固执而孤独地探索。
艺术家 | 段英梅
段英梅
她从小就抱定了学习艺术的梦想!能够从事艺术,是她一生中最希望实现的一个梦!曾经在东村生活的日子令她非常开心,对于生活中经历的困难毫不在意。当年的她在懵懂之时参加了《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创作,仅仅是因为能够正式参与到大家的行为艺术创作中就令她无比的高兴。如今的段英梅已经是具有国际声誉的行为艺术家,为了艺术之梦她还依然在不断追逐着。
以下为访谈内容文字整理,由观鲤台联合著名策展人杜曦云完成。
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你多少岁?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朱冥:1995年我23岁,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就来了北京,那时候我们家就给了我300块钱,我背了6个包就来了,当时什么人都不认识,只认识两个朋友,一个在中央美院读书,刚来的时候就跟他挤一个床,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找房子,城里房子贵得要死,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帮我,在现在朝阳公园那里找了一个房子,当时是15块钱一个月,就住了下来。那300块钱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就做很多的事情赚钱:做模特、画肖像、擦车、摆地摊,还自己挖野菜吃。
段英梅:当年我25岁,我家里人会给我生活费,差不多每个月500块钱,可是在当时还是不够。其实,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
杜曦云:当时的一些人没有体制里的工作,但又选择了留在北京追求梦想,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你当时是“盲流艺术家”吗?
朱冥:对,特别典型的盲流艺术家。
段英梅:那时候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艺术学院毕业的,所以就没想过自己会是什么“盲流艺术家”。我是石油学院毕业的,学的是采油工程专业,毕业后在采油厂当了一年技术员。后来,我就改行学画画了。当时在北京学画画就是很高兴,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梦想学艺术,那时候终于可以开始画画了,所以感觉像是在梦里一样。
杜曦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家里支持你追求这样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吗?有来自家庭或同龄人的压力吗?
朱冥:家里不知道我的状态,就是觉得男孩子应该出去闯,我就出来了,家里只是觉得我去搞艺术,但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后来过了很多年,家里才知道我是苦成这样,当时也没跟家里说,在东村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三四十块钱都不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是1991年来的北京,过了2000年生活状况还一直都不行,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有了一点点起色。当时没有来自家庭或者同龄人的压力,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可能会做一个冒险家、旅行者,后来画画以后,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风险画家,每天都可以出去,自由自在的那种状态,觉得不管怎么苦都喜欢那种状态,因为我的家庭是管束特别严的那种家庭,所以一直以来就喜欢脱离那个环境。
段英梅:我生下来发音就有问题,有很大的语言障碍,我不喜欢说话但喜欢画画。1991年,我21岁时,我爸爸带我来北京做了一个口腔大手术,手术后有三天老是梦到和艺术相关的,每天都和我爸讲我的梦。在家里我爸很偏爱我,在我住院期间去中央美院帮我找老师,希望我能学画画。就这样我认识了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杨建华先生,也正因此我便留在了北京开始真正的学习画画了。后来跑到东村是因为当时有个学艺术的男孩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想住在他的对门,就这样我就搬到了他住的村子,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东村。有一天,我爸妈来北京到东村看我,我爸看了我的画之后气的心脏病都要犯了,我妈也哭了,他们就后悔让我留在北京学画画。其实自从做艺术以来,我和我家里有过很多的摩擦,但都是因为我的一再坚持而没有离开。总的来说,我的家人还是非常理解尊重支持我做艺术的,而且我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做艺术,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我爸,我妈,我哥,我姐,我妹的大气宽容的帮助。
杜曦云:当初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吗?
朱冥:这么多人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一开始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的状态就是东村要散了,之前我们已经被抓过,抓了以后回来人员就很分散,但是既然在一起,最后就要有一个总结,于是讨论做一个作品作个纪念。
段英梅:关于作品的思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和别人聊过,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至于大家表达的思想是否一样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最让我高兴的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把我带上,就算每天只是帮忙我也会很快乐很满足。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大家说需要十个人,很高兴他们把我带上了。我那时比较单纯,从来没想过也没当过主角,我是那种喜欢站在别人后面,站在角落,做配角的人。这些年过去了,我其实还是喜欢这个呆在别人后面,呆在角落里,但我也学会了站在别人的前面。
我从来不想说当代艺术、现代艺术或者是后现代艺术,我只重视后面这两个字“艺术”。我要把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消解掉,只存在一个精神状态,这就是生命最后的意义。
--朱冥
没想过成功的问题。我几乎每天都处在在做艺术创作,我一直都感觉自己好像是活在梦里面一样。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致力于发展行为艺术与慈善领域相结合。
没有考虑名利之类。
当代艺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要看每个人的喜好,当然也可以和社会有一些链接,可以反映社会现象问题。
--段英梅
杜曦云:现在回过头来看《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对这个作品的解读有变化吗?
朱冥:我一直认为这件作品就是大家在一起的一个好玩的事,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我也没怎么看重它,后来大家开始看重它,是因为这个作品太有名了,有了利益以后就开始不一样了,本质就变了。
段英梅:当时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实际上对这件作品的很多细节我都不知道,我只是参与而已,但很高兴我和大家一样都有这件作品的版权。1998年,我在德国读书期间,给我的同学还有别人看过这个作品的图片,当时大家也都没啥反应。后来有一天这张图片突然变得很有名,当他们知道原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艺术家时,他们的眼睛都睁得挺大的。但关于这个作品有关它所表达的思想,我并没有刻意的再重新去解读。
杜曦云:当年你们做艺术作品时,是不是被周围的人视为怪物?据说有些人还被当地居民举报过、被治安人员遣送等,你有过这样的遭遇吗?
朱冥:那肯定被视为怪物的,对村民来说,看这些人每天白天都睡得很晚才起床,晚上就像夜猫子一样,走到路上到处都是垃圾,第二天低个头人又穷得不行,一个个都这样,头发又长,反正就是一帮很怪的人。当时跟周围的村民相处还挺好,大家好像也没有什么矛盾,只是觉得这些人有点怪,搞艺术的怎么搞成这样。当时有一个香港人来采访,我们做行为的有三个人,张洹、马六明和我,我们有个时间安排,先张洹表演,做完以后是马六明,接着是我。马六明做的时候警察就来了,突然上来把那个地方包围了,敲门很凶,一窝蜂就进来了,然后所有的人都蹲在那儿,当时有单位的人也很多,大概20-30个人吧,然后就一个个看身份证,有单位的当天就放走了,没有单位的就在那儿。最后审查到我们,张洹当时听到这个事情就跑了,后来好像是跑到东北去了。我们也没想过这个事情会有多严重,我也没干什么坏事,所以我没跑就在那儿,结果我跟马六明两个人就被关了,他关了3个多月,我是4个多月,到4个月的时候我被遣送去了湖北,在湖北又呆了半个月,然后家里拿钱赎我出去回了长沙。在看守所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一个单间,等于是隔离,其它的人都是睡通铺,我每天一个人,很多人看我一个人,觉得我肯定犯了巨大的罪,但我过几天就跟他们提我是艺术家,但也给他们解释不通,后来他们也烦了。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绝食,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有一天眼睛突然一下子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睛睁开后看不见,我当时就急了,以后搞艺术怎么办?于是马上问别人要吃的,那个窝窝头就跟喂猪的一样,我一次只能吃大拇指这么一点,拼命地往嘴里塞,喝了一碗汤,是那种漂了一点小肥肉的汤,后来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能吃两个拇指这么大的窝窝头了。当时想,我站着进来,就一定要站着出去。
段英梅:那时我们生活在郊区农村,一些老百姓应该接受不了我们做艺术的方式,肯定一些当地人老会在背后嘀咕这些做艺术的人。比如张洹做了个作品,裸体从家走到厕所,当然村民接受不了,所以后来把警察招来了。我也有过被抓的遭遇,那时住在我对面的是朱冥,当时他的家被警察抄了以后,顺便把我住的地方也给抄了,然后他们把我带去了当地的派出所,呆了24小时,后来没问出啥问题,就把我放出来了。刚放出来没多久,彬彬用脚把警察封的封条踹开了,然后她跑了。半路上,警察又把我抓进去了,扣在那里很多小时,也没问出啥,后来又把我放了。
杜曦云:当年选择这样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时,你觉得自己日后会成功吗?不成功怎么办?那个时期,你的内心痛苦吗?茫然吗?想过打退堂鼓吗?
朱冥:我有想过离开北京,但没想过会放弃艺术,因为好像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别的干不了。因为那时候接触的人很多,看到很多人性很卑鄙的方面,心里很凉,就想不在北京了,回老家算了,那是1996年,心里特别烦。并且那个时候好像经常感觉有人跟踪我,于是我把头发梳得很正常,低着头走路回到自己住的房子。这种心理斗争持续了半年,最后决定不回去了,死也死在这里,就是这样一直在北京。
段英梅:我没想过成功的问题,也就没想过不成功会怎么办。那时我一直对自己从事艺术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做艺术。从21岁开始做艺术至今,尤其是在我1998年来德国后,我几乎每天都处在在做艺术创作,我一直都感觉自己好像是活在梦里面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偶然,偶然的机会我开始从事艺术了,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东村,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德国,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从事行为艺术了,偶然的机会让我周游世界,去了四十多个国家……所以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几乎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象别人一样,我一直也都有烦恼,当时在东村时,除了个人情感方面的烦恼外,我也有艺术方面的烦恼和茫然。比如,当东村的一些艺术家做行为时,我也有做行为的念头,但是我从小就比较腼腆,所以不敢做,所以就觉得比较不开心比较痛苦比较矛盾。我那时已经画了好多年画了,但我发现只画画好像有点不够,好像还需要写画画以外的东西。东村实际上是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行为艺术?在德国跟随我的老师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Abramovic)学习期间,我得到了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除了个人作品外,我还做过70多件艺术合作项目。
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想过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吗?在那个无名的荒凉小山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你们十几个人,赤身裸体在做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的“荒诞行为”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朱冥:那时在做的时候,后果什么的这些都没想过,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成功。没有觉得荒诞,实际上我们也没想会具体在哪一个山上,就开车往这边走,走到一个比较荒的地方,好像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找了一个缓坡觉得比较合适就做了。一开始我们就想好了是怎么样去摞这个人而不会倒下去,不过我差一点掉下去了,因为我的体重是最轻的,所以是最上面那个,下面是两个女孩,她们中间有一个空隙,所以我的手要拼命地挽着,差一点就掉在中间,最后我坚持了有10分钟的样子,下面的人也在哇哇叫,因为地上长的那个枯草,有杆子扎在身上,上面人压着,下面很重,还有点冷,感觉他们一直在下面有点发抖。
段英梅:没想到会引发什么后果。当时做完《无名山增高一米》时,国外就有报道,因为张洹他们认识一些报社的人。我参加这件作品时特别高兴的是,他们做行为把我也带上了。在做之前,大家怕我笑,所以一再叮嘱我,但当时我没笑,他们好像挺多人都笑了。
杜曦云:《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经过多长时间才逐渐被人们认可?逐渐获得认可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朱冥:对我来说,我始终觉得这个作品只是一个纪念,就是大家在一起。
段英梅:我不太知道。我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后,都没有人知道或是提起过东村。后来到了2008年左右,才突然听说我因为这个作品在中国还挺有名的。我当然很高兴也很荣幸当时参与了这件作品。
杜曦云:《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成功,对你日后的生活有明显影响吗?
朱冥:对我没什么影响,因为做完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还要做自己的作品。
段英梅:现在看来,其实北京东村给我的艺术生涯带来了很多有利的地方,包括这件作品。
杜曦云:社会上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当代艺术,你觉得应该怎样向更年轻的85后、90后介绍当代艺术是什么?
朱冥:我从来不想说当代艺术、现代艺术或者是后现代艺术,我只重视后面这两个字“艺术”,我关注的是怎么去实现和实践这个东西,不管它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帽子,我只做艺术,不管材料和方式,就是去实践,然后按自己的方式一直走,因为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追求,有一个自己定的终极目标,然后就去完成就行。
段英梅:实际上我很少回答这个问题。但当代艺术可以增加人的视野和知识面,只要不断地尝试去做,会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无穷的创造力等等。
杜曦云:您对当代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例如文化倾向、艺术的多元化、是否与社会现象问题关系紧密。
朱冥:我认为好像当代艺术跟社会接得很紧,但我可能不属于这个类型,我离社会很远,我就在自己家,自己一个人去做艺术。我一开始就认为有一个人类的终极目标,我在做这些东西,不管它是什么艺术,我就按自己的路走,我觉得这个终极目标是一种精神,一种很虚的精神,我要把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消解掉,只存在一个精神状态,这就是生命最后的意义。
段英梅:这要看艺术家的创作作品的出发点和作品的方案。我个人认为当代艺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要看每个人的喜好,当然也可以和社会有一些链接,可以反映社会现象问题。使用任何一种艺术媒介都可以创作出非常好非常当代的艺术作品。任何一个材料都是非常好的材料,使用任何一种材料都可以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
杜曦云:能否介绍《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之后你自己最满意的自己的作品?
朱冥: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一个关于发光体的作品,就是身体上涂了荧光粉,然后通过灯光照射以后,人体是发光的,就像一个灯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延续,慢慢消失在黑暗中,这个作品从1998年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做。我目前一直持续做的就是气球和发光体的作品。
段英梅:其实在《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作品之后,我做了很多我非常满意的作品。2010-2011年间,大约8个月,我完成了风铃草林儿童安养院的行为艺术项目,我的目标是把行为艺术和慈善紧密结合起来。在风铃草林儿童安养院的我还做了7周的居留,这段时间里,我不仅仅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工作,同时我也是一个志愿者。在这段时间里,我致力于发展行为艺术将其与慈善领域相结合。风铃草林儿童安养院是一个令人十分着迷的地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经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让生命有限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住在这里一段时间,给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带来了轻松愉快。每天我都和安养院里的人进行交流,也和这些特殊的家庭约好,坐下来和他们聊他们自己和孩子们的生活,主题包括童年、家庭、假日等。在此期间,我也会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画简单的图画,来呈现他们的故事。我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谈能够让人们有机会谈谈自己的感受,了解他们对孩子的希望和恐惧,也很希望能够对彼此多一些了解。通过和一些孩子们的接触,如果他们不能从生理上参与到我们的合作中来,我会尝试让他们以其他的方式参与进来。这些会面富有成效的且有理疗作用,让我们一起度过有意义且快乐的时光,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单单经常与这些父母和孩子呆在一起,我还和安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工作人员是安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那里和曾经住在那里的孩子一起经历了很多。让他们也有机会去讲述那些曾经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共同经历。观察,帮助,谈论和研究都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还与不同家庭和工作人员合作了24幅油画,这都将成为我赠与儿童安养院里一些看得见的财富。另外我还创作了两本童话书,灵感来源于我在那里认识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