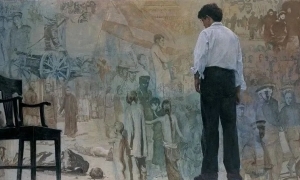罗发辉作品
由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主办,上海华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唯一协办、《成都商报》和《新闻晨报》联合承办的“依然香如故———何多苓、罗发辉、李强三人作品展”10月17日~28日将登陆上海洛克·外滩源协进大楼,展览将推出三位著名当代艺术家的23幅油画和7幅色粉画作品。按照策展人、成都商报艺术投资总监王奇的说法,这次的展览“纯属偶然”。
以花为媒,以传递内心为本,以典雅的绘画气质为线索,是本次大展的特征。何多苓坚持以杂花写生的方式直接与自然交换,是他近年来的一种有效而重要的尝试;罗发辉则希望自己作品中对“欲望”和“阴郁”的探秘更为准确和深邃;李强的花卉系列则更多是冲着传统文化去的,来源于他对传统的认识和创作中“完全彻底的陶醉”。
此外,作为大展的支持单位,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技术积淀和自主创新,以“永远为您多想一些”的服务理念,成为中国大陆电梯业前五大生产商之一,恪守信誉且追求完美的形象,与本次大展的理念十分统一。
何多苓:花是奇迹
“我相信偶然进化。就像《带阁楼的房子》里的‘画家’说的,不要光是相信什么残疾人突然站起来是奇迹,其实每个人都是奇迹,花是奇迹,星星也是奇迹。”
以人像为“永恒主题”的何多苓现在每天都画花的写生。何多苓说,画花是他训练自己的手段,单纯到只需要手,不太需要大脑,不用考虑,“直截了当地与自然交接、互换”。
如果说何多苓之前的人像作品是对那个激情年代的青春书写,那么如今的杂花系列更像一种忧郁的媒体,传达着那个年代的回响。对肖像十分迷恋的何多苓一直希望保持一个状态:独处一室安静地绘画,单凭画画本身获取最大的愉悦。何多苓每天都会去位于三圣乡的“带工作室的花园”,像上班一样,执迷于花园中那每天不停变化的时间,从之前喜欢享受花园里的常青,变成同样享受冬天的萧瑟,甚至让自己过得都“模仿自然”。
2010年开始,何多苓开始尝试真正文人化的融合与表达:将中国水墨画的手法成功地转换到作品中,具有写意的韵味,又有当代语境。他每年春天的一个固定项目,是找一天出太阳时出去买树、买花草,按照自己构建的花园模板创建一种理想化的实验园,然后让自己的创作跟着这种“实验”一起变化。艺术家带领观者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画画的基础修辞———写生上面,回到花花草草,回到每个观者都看得懂的时态:当下。所以,有时候能从他的花中看出惊惶少女的倒影,有时则可以看到带着可爱莽撞气息的玫瑰。
著名策展人鲁明军说,单从何多苓的画面看,不难体会到他对书写的自觉,但与传统写意不同的是,他对画面形式及内在的要求非常苛刻。“与其说他是画家,不如说他是个诗人,从他早年的《春风已经苏醒》《青春》到今天的《杂花写生》,画面中的文学性、抒情性或者说诗性,特别是画面所透露的孤寂、脆弱、敏感、忧郁、伤怀、神秘的情绪和气质几乎贯穿了他三十余年的言路和心路。”
罗发辉:花即内心
“我几乎每天都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当下社会生活的环境信息,很多都带有伤痛的因子。这些作品来源于我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和转化这些经验的能力。”
罗发辉画作中带有“浮世”和“物语”感的大花、赤裸女性和花朵上空的阴霾,都是他对现实的观察。
他画玫瑰,却不为表达爱情;画艳俗的裸体女人,却不为呈现性感;画血色伤口,又不为表达痛苦。“我几乎每天都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当下社会生活的环境信息,很多都带有伤痛的因子。这些作品来源于我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和转化这些经验的能力。”罗发辉说。花朵与花朵所指代的女性,呈现出一种阴郁而略显扭曲的形态,这是罗发辉另类的艺术感知。
罗发辉并不否认“玫瑰”后来成了他绘画的一个符号,但这种“玫瑰”似乎又不止爱欲与纠缠那么简单。通俗地说,他的大花作品代言了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悲伤和丑陋欲望。花即内心,而他的表达方式是张牙舞爪的,是对抗式的,硬碰硬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大花作品,其花瓣的厚度、色泽、开放的姿态和画面中那些被抛却了表情的男人、女人的姿势———搂抱、躺、坐、侧卧等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置身罗发辉的画室,他很少会给你讲述绘画的所谓理论,而是不断地表达他的想法———这幅大花是送给某人的,那幅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他还会给你讲,他置身于荷兰一个巨大的音乐节现场,被DJ调动到亢奋不已的状态,然后是那种不断陷入的狂乱感和身不由己;或者他又突然跳到川美门口一家著名的苍蝇面馆,一碗小面也会让他的味蕾和内心激动不已。
李强:借花传情
“如果说我现在的这些作品和传统的中国画有某种相似性的话,我想这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我并没有刻意在绘画方式上去生硬的借鉴传统元素,只是希望通过花卉这样一个题材去追寻或者说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指涉的生命关照,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的现实所缺失的。”
习惯晚饭后钻进画室,不容打扰的李强通常会用通宵的时间在画布上表达自己即兴的“纠结”。
“之前我一直很在意画花的材料和语言,当作品越来越具有装饰性后,我发现无路可走,必须跳转。”于是,在经历了风景画阶段后,李强的花卉作品呈现出“朦胧而不虚幻”“东方而不模古”的明显特色。李强甚至认为这些花是可以编造出来的,喜欢玉兰,他可以画一丛玉兰,让画面变成脱离花和花丛的生物性;喜欢牡丹,他把牡丹的所谓“富贵感”等外化的意味全部褪去,自然呈现一种植物的本态。和艳俗完全无关。艺评人的观点是,李强的作品表现了他作为画家内心的感受,并由此发现了花卉本来的性格。
按照李强自己的说法,之前他的花卉作品是“借题发挥”,而现在更重要的是“借题传情”或“借表达意”。著名批评家王林认为李强把中国花鸟写意画的造型特征、留白方式和流畅笔法运用到画面,但他作品中的东方情调和抒情意味则和传统的中国画并不关联,它们本质上呈现的是经典油画的肌理质感和审美情趣。著名批评家鲁虹则认为,李强一方面有效地将东方写意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统融合,另一方面还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们长期希望解决的若干艺术问题。
“如果说我现在的这些作品和传统的中国画有某种相似性的话,我想这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我并没有刻意在绘画方式上去生硬的借鉴传统元素,只是希望通过花卉这样一个题材去追寻或者说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指涉的生命关照,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的现实所缺失的。”李强不愿意过多谈论他的花卉作品的所谓技法和意义,但这毫不影响他对自己作品中色彩、笔法、氛围营造、浓淡的控制。他作品中深具的东方情调,想必就来自于这种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