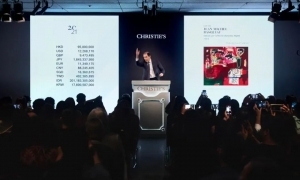在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中,光影与几何的现代秩序,与中国园林的古典意境相互交织。艺术家何多苓的个展“人在春山外”在这里找到了最为契合的语境。这个引自欧阳修词句的标题,不仅是何多苓一件作品的名称,更概括了他数十年来的艺术追求:在与喧嚣现实的“错位”中,在画布上构建一个可供栖居的精神家园中,主动的“逃离”,成为艺术家在时代洪流中为自我保留的一份珍贵独白。
6月24日至9月7日,“人在春山外——何多苓作品展”于苏州博物馆举办。何多苓的艺术始终与文学,尤其是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早期以穆勒等西方现代派诗歌命名,到近年有意识地援引中国古典诗词,他一直通过文学的暗示,在当代与古典的悠远意境之间,构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本次展览特向中国美术馆借展《春风已经苏醒》和《雪雁》这两件在中国现当代美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展品。从《春风已经苏醒》到近期作品《人在春山外》,从深受安德鲁·怀斯影响,画风细密清晰,如同工笔,到后者转向更为模糊、含蓄且在精神气质上更贴近中国画的“写意”表达。我们得以看到伴随着艺术家年龄与心境的沉淀,在审美趣味上的自然演化。
展览开幕之前,99艺术、K空间创始人杨凯与何多苓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谈,从主动选择与时代的“不同步”到对“隐”的追求;从古典诗词到现代音乐;从西方建筑到东方造景……一位艺术家数十年来的文化立场与对绘画的热爱缓缓铺陈开来。

左:何多苓
右:杨凯
Q&A
杨凯:
这次在苏州博物馆的展览标题“人在春山外”引自欧阳修的词,同时也是你的一件作品的名字。这次展览举办的契机是什么?这句词跟你的作品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隐喻关系?
何多苓:
这次展览的名字“人在春山外”是美术馆定的,不仅引自欧阳修的词句,也正是我一幅作品的名称。
我早期的一些绘画采用西方现代译诗进行命名,近几年,我有意识地选用大众熟知的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作品的名字,我想通过这种形式,让传统与当代在意境上产生一种对话。在我的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人物、服饰还是景物,都是当代的绘画语言和视角,意在将古典诗词的悠远意境与画中描绘的现代生活场景进行并置,产生新的意义和观看角度。
我希望将古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感怀,与我画作所呈现的当代体验并列,以探寻二者间的矛盾与共鸣。“人在春山外”所蕴含的那种超然、寻幽的意境,在喧嚣的现代社会中或许已难寻踪迹,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在古典文学浸润下成长的艺术家而言,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也是艺术思索中无法回避的维度。“人在春山外”并非纪实性描绘,而是象征性地将画面引向一个遥远的精神层面,获得一种在现代生活中难以企及的慰藉。这种精神上的体验和追求是永恒的,也是我们当代人所需要的。

《人在春山外》
200 × 300 cm,布面油画,2022

《兔子夏洛特》
160 × 300 cm,布面油画,2011
杨凯:
艺术家一方面往往要超然于物外,但一方面当代艺术又无法与现实生活割裂,所以,在你近几年的绘画创作中,如何捕捉个人感受与时代洪流之间的“同步”与“错位”?
何多苓:
我觉得我是在追求一种“错位”。个体生命与所处时代更多的是同步。无论是社会风尚的变迁,还是公共空间的异化,都构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背景。比如苏州园林,其营造初衷在于“幽静”二字,但在当下,白天的人潮早已消解了这份意境,使其与初始功能产生背离。
然而,艺术创作赋予了艺术家一种权力,在画布上,我可以选择与时代“不同步”,甚至刻意疏离与背离。艺术的自由体现在选择的主动性上,我可以选择不复刻周遭的喧嚣,转而规避和滤除某些元素,去营造令我内心愉悦、并足以赋予生命价值的精神场景与意境。
不同代际的艺术家需要构建契合其时代感受的不同画面。我的绘画并非表现或再现当代生活的现实,而是刻意与之保持距离。这是一种创作上的疏离,也是艺术家所拥有的一份不受现实生活所束缚的自由。


“人在春山外——何多苓作品展”展览现场
苏州博物馆,2025年6月24日-9月7日
杨凯:
从古诗到现代诗,你是如何将诗词的意境,包括气韵和精神,转化并呈现在油画这种媒介上的?
何多苓:
从80年代起,我一直在实践虚构与现实,画面与诗词的“转化”。我始终与现实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当然,我并非对现实漠不关心,相反,我高度关注现实,因为它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关注不等于要进行直接的、纪实性的描绘。
2008年,我为汶川地震创作的《偷走的孩子》,算是我唯一一件与重大时事直接关联的作品,但我也并没有选择用纪实性的方式表达。这幅画中,我使用了更为符号化与诗性的语言,比如用脆弱如铁丝的线条暗示扭曲的钢筋,以混沌的背景营造氛围,并将视觉焦点置于幸存儿童凝固的惊恐表情之上,来捕捉一种超越新闻报道的诗意。
绘画的功用有别于新闻或纪实摄影,我更希望艺术能提供一种如诗歌般的表达。无论是以西方当代诗歌与音乐为标题,还是从中国古诗词中寻找意境,本质都是通过文学性的暗示来构建画面的精神性。这是一种更疏离、更纯粹、更个人化的精神探索。

《野园》
200 × 150 cm,布面油画,2011
杨凯:
这次展览特意与苏州的地域文化及园林“借景”模式相结合。你也戏称自己是一个业余的景观设计师。展览选择展出哪些作品、如何布展,是否会受到苏州博物馆的特定空间和文化语境的影响?
何多苓:
最早计划做这个展览的时候,除了苏州博物馆,还有一个更大场地、能展出更多作品的空间,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贝聿铭先生作为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师,其谱系与柯布西耶、密斯等大师一脉相承。然而,他的华裔身份,以及与苏州(其祖宅狮子林便坐落于此)深厚的家族渊源,为他的创作注入了复杂而深沉的情感。他将现代主义的几何性语言,与中国古典园林非几何的、讲求意境的传统进行了精妙的融合。
贝聿铭先生将苏州博物馆含蓄地融入到苏州古城的肌理中,达到了一种“大隐于市”的境界。步入其中,轴线、借景、月亮门等传统元素的几何化转译,又彰显出现代建筑的内在秩序。我能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举办个展,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次展览的主题、作品与空间叙事,均围绕苏州这一特定地域文化语境展开。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与策展团队共同挑选了一系列探讨人、自然与文化关系,并力求呈现古代意境与当代精神相融合的作品,包括《春风已经苏醒》,也被借来进行展出。
为了这次展览,我在苏州进行了采风与创作,也尝试了一些新的视觉实验,比如将拙政园的太湖石等典型苏州园林的符号引入我的个人艺术语言之中。

左:《拟江南No.1》,110 × 80 cm,布面油画,2025
右:《拟江南No.2》,160 × 100 cm,布面油画,2025

《春风已经苏醒》
96 × 130 cm,布面油画,1981
中国美术馆 藏
杨凯:
从《春风已经苏醒》到你的近期绘画,有人说,你的画风越来越松弛,画面也越来越空旷,这种变化是你主动寻求的结果,还是随着年龄与心境自然演变的?你如何看待这种创作状态的转变?
何多苓:
这与年龄、阅历及心境变化都有关系。我觉得可以用《春风已经苏醒》与《人在春山外》做一个对比。无论是取自德国诗人穆勒的诗句命名的《春风已经苏醒》,还是如今援引欧阳修词句的《人在春山外》,都是以诗歌为题,追求我所理解的“诗意”,而并不是对文字进行直接的图解。我所追求的“诗意”,是一种不定性、非叙事、甚至略带晦涩的视觉呈现,是画面与标题之间形成的错位感与张力。
当然,这两件作品在绘画语言和美学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画《春风已经苏醒》那个阶段,深受安德鲁·怀斯的影响,画风细密清晰。随着年龄增长,审美趣味也在变化。如果说怀斯那种画类比于中国的工笔画的话,那么现在我可能更喜欢写意的风格,所以大家看到我近期的作品转向了一种更为模糊、含蓄的表达,在精神气质上更贴近中国画的“写意”传统。
这次展览,将这两件分别代表我艺术生涯早期与当下的作品并置展出,我觉得很有意义:不仅构成了我艺术人生的“一个开端”与“一个阶段性总结”的跨时空对话,更清晰地勾勒出我作为艺术家的完整历程。这其中既有技法与风格上的变化,更有贯穿始终、沉淀为我个人印记的那份源于性格与审美气质的、对“诗意”的永恒探索。

《白屋山居图》
200 × 100 cm,布面油画,2022
杨凯:
我看到很多评论称你为“士者如斯”,作品中蕴含着一种内敛、优雅的“士人精神”。你所追求的“士人精神”是什么样的?
何多苓:
我觉得我没有中国士大夫的精神,要说跟“士”这个字沾点边的话,可能是“隐士”。我对中国特有的“隐士文化”很感兴趣。这种文化现象,根植于数千年的历史与政治传统,在世界其他文明中很少见。文人选择主动将自己“藏”于名山大川,在与尘世的疏离、隔绝中,追求一种如“人在春山外”、“空山不见人”般的超然意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代表有很多,即便是苏轼这般曾经位极人臣者,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与成就,也是在被迫的“隐逸”生涯中创造。
这种对“隐”的追求延续至今。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著作《空谷幽兰》在中国引发巨大反响,但是在美国根本卖不掉。然而,波特笔下终南山的现代隐居修行者,与我所理解的传统“隐士”仍有区别。我所心向往之的,是以王维为代表的,将深厚的文化修养与避世姿态融为一体的古典文人。这一脉“隐士”谱系,构成了中国文化中一条独特而深刻的精神脉络。

《石榴残》
200 × 150 cm,布面油画,2021
杨凯:
艺术家是一生的事业,自我更新是创作不衰的重要动力。除了诗歌,在你的创作和生活中,还有哪些能为你带来养分的领域和爱好?
何多苓:
音乐在我的认知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绝对精神性的存在。我从70年代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听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少时初闻经典所带来的震撼,甚至超越了日后听顶级音响或音乐会现场的体验,这是“第一次”的启蒙带来的震感。
我认为音乐是人类唯一的、纯粹的精神性独创。视觉艺术的美,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本就存在的美的世界。从宇宙的宏观秩序到一朵花的微观构造,美的形态早已由自然提供。艺术家的工作,无论如何抽象或转译,其实都很难完全脱离这些被自然赋予的美的形式。
音乐是人类凭借智慧与情感,将无序的噪音,通过高度复杂的技术与思想,建构成一种能带来最高贵愉悦的、有序的结构。我在画画的时候是要听音乐的。对我来说,来自音乐的精神滋养远大于任何图像所能给予的启发。

《玉阶空伫立》
200 × 150 cm,布面油画,2022
杨凯:
音乐的节奏、韵律,会影响你的画面吗?
何多苓:
画画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肌肉记忆,这个肌肉记忆里,我觉得是包含音乐的。
音乐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像康定斯基那样,画面色彩、结构与音乐产生了一种可视化的结果。对我来说,长年累月听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肖邦……,这些音乐的精神内核已经植入到我的意识深处。我觉得,精神性的浸润,最终会转化为一种生理性的惯性,在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影响着我的身体与笔触。
我曾经与音乐家做过交流,我们都认为音乐与绘画,尤其是交响乐与油画,在结构层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音乐是会影响画面的,只不过不同的艺术家会有不同的视觉表现,比如当代青年艺术家在创作时听摇滚乐,他们画面呈现的节奏、张力与质感,也必然会与摇滚乐的特质产生关联。

《云深不知处》
200 × 100 cm,布面油画,2022
杨凯:
我注意到你工作室里有很多看似未完成的画,这种“空”的构图是刻意为之吗?你如何解读作品中的“留白”?
何多苓:
对我来说,“留白”是天性,与中国传统的隐士精神一脉相承。我觉得隐士的人生,就是一种诗意的“留白”。
我最初对“留白”的认知,实际上是源于怀斯。他的作品中常有大面积的“留白”,这在西方绘画中其实是极为罕见的,我甚至一度认为在这一点上,怀斯是有中国文人气质的。也正因如此,他在美国当代美术史中占据着一个既特殊但又边缘的位置。
在他的启发下,我曾进行过极为前卫的“留白”实践。例如,我的一件早期作品《天空下的孩子》,画面中绝大部分是作为天空的灰色留白,仅在下方有一个人物的头部。这种表现形式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
我记得是在1989年前后,我的作品在美国展览的时候就有西方观众表示,他们难以理解藏家为何要为“空白”付费,认为画布应被填满才算完成工作。
这其中体现了东西方艺术观念的差异。中国传统文人画中,“留白”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计白当黑”,空白与笔墨,是相互对立又共存的关系,有时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
当然,我是很认真地画这些“留白”,不是简单地把一部分画面空出来这么简单。它不是“无”,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有”。

左:《观鸟》200 × 100 cm,布面油画,2023
右:《赏花》200 × 100 cm,布面油画,2023
杨凯:
在这个消费主义至上的时代,绘画是否成为了你作为艺术家追求自由的一种抵抗?
何多苓:
在我看来,所有真诚的艺术创作,起点都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无论是选择直面并描绘民间疾苦,还是如我一般,追寻一种源于自我的审美愉悦,这两条路径在创作的本真性上并无高下之分。有些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或许充满了挣扎与痛苦,但这同样是他们忠于内心的选择。而我的选择,是将绘画作为一种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的愉悦过程。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刻苦,每天比你学生画的还多。我说,我这不叫刻苦,因为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愉悦的。
曾经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博士生批评我的画作缺乏批判性与斗争性,还没等我回应就有另一位学生站起来反驳,认为我的画能给他带来愉悦、放松与慰藉。我觉得,这恰好点名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
归根结底,一切艺术创作在出发点上都是“为自己”。艺术家无法真正预设他人的需求,唯一可行的,是忠于自我,并将其真诚地呈现出来。当观者自身的感受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产生共鸣时,作品的价值便得以实现。

《近黄昏 No.5》
200 × 300 cm,布面油画,2020

《无意苦争春》
400 × 300 cm,布面油画,2020
杨凯: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去跟那时的自己喝一杯?
何多苓:
相比大学等其他人生阶段,对我来说,做知青的那些年是最难忘的。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偶然回溯,还会带来一种超现实的、仿佛精神穿越般的感情。那些不期而至的画面——天空、草原、山峦……在漫长时间的过滤下,已化为一种自带穿越感的意象。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就如我那时目击过一颗彗星,它带着梦境般的质感,以至于我一度怀疑它的真实性。为此,我还进行了求证。我先是查阅彗星年表,确认了当时确有一颗非周期性彗星造访太阳系;又与当年一同下乡的同伴追忆,也印证了我们共同的目击记忆。所以,在漫长的时间沉淀下,这段记忆已转化为一种主观的、像梦境般的精神体验了。

《雪雁》
15.5 × 22.5 cm,纸本丙烯,1984
中国美术馆 藏
杨凯:
面对层出不穷的年轻人,你会有创作上的压力吗?
何多苓:
没有压力。我始终强调,在艺术中,要有“进化论”的心态。年轻一代不必也不应重复我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拥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审美,并以此构建起一个全新的艺术生态与市场。这是一种健康且正常的迭代。所谓一代一代艺术家之间的“代沟”,其实是推动艺术向前发展的动力。
我觉得,当代青年艺术家的绘画,呈现出与国际艺术潮流日益紧密接轨的趋势,但在画面的组织方式上,我发现很多也在运用超现实与碎片化的组织方式,这与我们老一辈艺术家是有共通之处的。青年艺术家倾向于运用鲜亮、饱和的色彩与碎片化的图像进行直接组合,在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中获得属于他们时代的、崭新的意境与愉悦感。
我觉得,年轻一代的艺术与我们不同才是最值得庆幸的现象。倘若一代一代的人都在画同一个画面,那才是悲哀。

左:《杂花写生系列》,100 × 50 cm,布面油画,2025
右:《杂花写生系列》,100 × 50 cm,布面油画,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