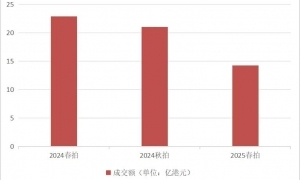“1993 年,中国部分现代艺术家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奋斗中的理想—大陆现代艺术家和作品首次参加了1993 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像这种在西方公认为是现代艺术权威性的展览,参展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多属于当时走俏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在创作取向方面,艺术家习惯根据国际性标准—可以说为西方艺术的一般观念创作。”—邹建平1996年发表于《画廊》杂志的文章《现代主义:失落的金苹果》,如此记述中国艺术家参加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产生的争议。在栗宪庭的策划下,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等艺术家参加了本次双年展。
此后,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在连续几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炮而红,成功走向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F4”。
而16 年后,因为第53 届威尼斯双年展《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单元,“F4”再次聚首威尼斯,通过艺术手法再现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当年介绍过的古代中国。张晓刚用马克笔在3 幅图片上用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抄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片段,岳敏君则在一个圆盘上构筑如同东西方交流和误解的迷宫。
重新聚首时,当年的热血青年已经成为千万级的艺术富豪,但也有些艺术家们还在重复十多年前的创作,则是更大的心酸。
马越说,自从2008 年自己那本自传体小说《长在宋庄的毛》出版后,他几乎成了宋庄的代言人,那些以前不了解宋庄的人,现在都来找他讲宋庄的故事。尽管最早来到宋庄的人,是方力钧、刘炜等1994 年到来的几个人。
马越边说边点燃一根ESSE 烟,抽这种女士烟是他今年春天开始的尝试,他说栗宪庭也受他影响改抽这个了。
41 岁的马越是1997 年来到宋庄的。他于1968 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就喜欢画连环画中的英雄人物。1995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画室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做了一个自由艺术家。此时,宋庄的故事刚刚开始,由于政府治理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居住地,随着方力钧、刘炜等几个艺术家的到来,宋庄小堡村,这个距离北京市区20 公里的偏远村落,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新的地理坐标。马越通过借来的近2 万元钱,也在宋庄拥有了一间院子。
没有人想到,这个多年来只能靠930 路公交车到达北京的村镇,在十年后可以通往整个世界。
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实验
现在定居宋庄的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说,宋庄艺术区的形成完全是因为偶然,就是艺术家们想找一个安静且便宜的地方创作。而宋庄,不仅安静,还有便宜的大房间和大院子,适合画画。在这里,独门独院分散了聚居于此的艺术家,圆明园时期大杂烩的景象消失了,艺术家们在宋庄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就像栗宪庭在他的文章《只是想住农家小院》中所说: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实验。从宋庄开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开始了正常的自由艺术家的生活,包括创作、展览以及和外界的交流上,乃至艺术品交易上,基本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群落和方式。
但如果用更简单的方式理解,宋庄的形成又只是适者生存的结果。
在圆明园时期,方力钧、岳敏君为代表的“玩世主义”已取得盛誉,当艺术家们从圆明园来到宋庄时,过去平等的流浪社会模式已经不再存在,已取得成功的艺术家自然很少和圆明园后转来的艺术家来往,泾渭分明,一个个“圈子”从此形成。大部分艺术家在酒精、赌博、女人中寻找慰藉,过着“浮生如梦,醉生梦死”的生活。
那时的宋庄,艺术家们主要面临两大问题:生存与艺术。多数艺术家靠打短工或兼职为生,比如代课,画行画,接设计、雕塑小活,开小饭馆等。平时的生活内容也很简单:聚会喝酒、聊天、画画。
一位艺术家回忆说:“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大块烤肉、大碗喝酒,一切眼花缭乱而有滋有味。生活是不确定的,被一种强烈的氛围包裹。”“那时也不太恐惧,只是觉得很难,很无奈,”马越说,“但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和理想,总觉得说不定哪天自己的画就会被人欣赏,自己会成名,基本就是生活在精神世界中。”
为了等到这一天,马越也想尽各种方法支撑生活,他做过群众演员,给歌厅做过装潢,画行画卖给小画廊,运气好的时候偶尔也能卖掉一两张画。更多时候只能靠画家朋友之间帮忙。“2003 年我儿子出车祸进医院,肇事方把孩子送到医院就跑了,住院费押金需要2 万元,我就问两个画家借了钱。画家们之间都很热心,我借给过别人钱,也有很多人现在还欠着我的钱。”
2006 年2 月宋庄艺术家的一次聚会。
画家和妓女一样,都是些没有安全感的人
这样的故事,充斥了马越的整部小说。在小说中,一个叫王思丁的艺术家写下这样的日记:“残酷的现实逼着你,一步一步去做你不喜欢的事,而我天生就喜欢顺着内心去做事。总以为我不怎么需要钱,对吃、穿、住也没过多要求,只是喜欢有一个空间,能安静画画就好。而现在,现实告诉我有钱才能画画,没钱颜料都买不到。”
这是宋庄艺术家的无奈。马越说,虽然艺术家在宋庄买了房子,租了土地,举家迁到这里,有的甚至老中少三代都在这里生活,再也不用流浪,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其他宋庄艺术家一样,虽然找到了家的感觉,但却总是住不踏实,生怕哪一天再出现几个方头大脸的人把他们赶走。
“画家和妓女一样都是些没有安全感的人。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戴上安全套也不会有安全感。”马越在小说中写道。生活在2005 年出现转折。那一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突然启动,资本改变了游戏规则,买画的人推开了艺术家的大门。宋庄一跃成为世界“前卫艺术基地”,艺术家们也开始“卖画、盖房、换车、娶老婆”的集体大跃进。
马越的生活也在那一年发生巨变。那年11月的一天晚上,马越和几个画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一个朋友带了位印尼画商过来玩,结果画商就看中了马越的《蹲系列》,一下子买走了全部20 多张画。卖了画的马越赶紧换掉老抛锚的北京吉普2020,花了6 万元买了夏利系列的高端车。买完他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跟上宋庄艺术家们的速度。有人一年换了3 次车,有人在宋庄买了更大的院子,有人搬到了城里。
“第二年我只好把车换成了斯巴鲁,”马越说,“因为他们的车都比我好,一起出门开夏利追不上。”
到了季节了,果子就噼里啪啦往下落
包括马越在内,今天的宋庄生活着超过3000 名艺术家,一年艺术品交易额达2.5 亿元。据《生活在宋庄》第四回展览负责人张海涛的调查,在这些艺术家中,有15% 的艺术家是传统写实绘画风格,30% 是现代主义风格,5% 在从事电影、音乐或写作,1% 从事摄影、录像或行为艺术,剩下超过40% 的艺术家在创作政治波普、艳俗、玩世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真正发财的是少数,”马越说,“当年从圆明园过来的,10 个里头只有一两个起来了。”更多人,一直卖不出画,过着清贫而普通的生活。“他们不是画得不好,而是准备不充分,在艺术市场大潮到来前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潮来了又不愿意模仿别人,画那些大哭或大笑的光头。”
“不过他们才是真正搞艺术的。”马越说。
1999 年入住宋庄的艺术家邝老五则对宋庄有更多悲观的观察。“在当今宋庄,你会看到来往穿梭的高级轿车和炫耀着金钱的诱惑,看到一座座美术馆在炫耀着和艺术无关的文化艺术产业,看到批评家和艺术家步履匆匆的赶路好像在追逐一个近在咫尺的目标。”他在一篇名为《宋庄的容颜》的文章中写道,“更年轻艺术家刚到宋庄就直奔成功者而去……”
邝老五认为,宋庄的一种气场在消失,宋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艺术家、批评家们没时间潜心研究,更没时间去深沉思考,把大多数时间消耗在应酬艺术资本家、艺术投机客和商人的俗人俗事当中。
马越则认为“人生如戏”,这是宋庄发展的必然,谁也无法改变。
8 月底的一天,马越为艺术家朋友张建俊主持了婚礼,38 岁的张建俊娶了一个小自己12 岁的新娘,艺术家们也在酒桌上聊起了艺术圈这两年出现的“老夫少妻”现象。讨论到最后,艺术家们得出这样的总结:以前,艺术家们都在流浪,结婚离婚,有人退出,有人死了,直到现在才安定下来,都已经四五十岁了,才在宋庄找到一点繁衍生息的感觉。“到了季节了,果子就噼里啪啦往下落。”
马越也一样,两年前他选择离婚,现在和一个80 后女孩一起生活。他尝试戒烟、戒酒,并会谈起老婆、体检、旅游之类的话题。他说这群人都会怀念圆明园那种充满激情的造的日子,但如果真要选择,肯定还是更愿意冷静地画画,过正常人的生活。
“宋庄应该会这样延续下去,”马越在抽了大半包烟后说,“新的艺术家可能会找到更适合、更便宜的地方,但我们已经在这里扎根了,迁是肯定迁不走了,有的人都死在这了。”
【编辑: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