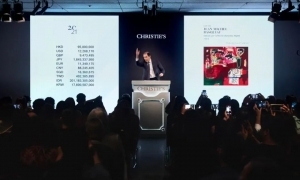水+墨展览现场 张建君作品
在当代艺术批评领域,水墨话题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领域。2000年以后,水墨的争论已经从简单的传统与现代之争转化到更复杂的语境,创作也从要不要现代转到如何现代,艺术家和评论家也从简单的批判传统转到如何在批判中发展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于2012年5月15日举办了“水+墨”展览就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次“水+墨”展览邀请的八位艺术家,既有参与早期1980年代、1990年代活跃的、出色的代表性艺术家,如陈心懋、 张健君、 王天德、王南溟、陈光武和潘缨,也有现在刚成长起来的、具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如李周卫和刘永涛。参展艺术家以上海为主,也有来自有北京和广州的艺术家。这八个艺术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从观念的角度,批判的角度,抽象的角度,书法的角度,人物画的角度和自然景观的角度,在水墨这一领域里面进行实验。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陈心懋的画风开始发生了转变。他的作品以历史古迹字体为背景,结合民间艺术和古代丧葬文化的一些元素,创作了一些抽象风格的综合材料作品如《史书系列》。在这组系列作品中,陈心懋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综合材料的实验,除了使用水墨和宣纸外,他还使用文字、麻纤维、石膏粉、橡胶、塑料等材料来进行语言的探索,画面肌理斑驳,像岁月的流逝,有种沧桑历史感。皮道坚在主编的《中国水墨实验二十年1980-2001》一书中认为在陈心懋的实验水墨作品中,“实物与平面结合,墨迹与拼贴组接。一方面,他使用传统的笔墨材料,却介入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他引入了多种非传统、非绘画性的材料,却又保留了东方审美理念。”可以说,抽象水墨与综合材料的交错互渗,是陈心懋从事水墨探索的一条主线,《史书系列》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也不断发展和深化。如《史书系列-错版》作品,巫鸿在《作品与展场:论中国当代艺术》一书中认为“陈心懋的《史书系列-错版》所显示的是未完成、局部涂污、有意错印的木版印刷品,经典著作的残迹或线索以被污损的影像和碎片的形式呈现出来。墨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文本与视觉形象之间的含混:这个材料被相互抵触地使用,既用来复制文本又用以使文本模糊,有时形态各异、随意渗散的墨渍甚至湮没了字迹。”1本次展出的《史书系列》为陈心懋自2000年以来创作的作品。陈心懋以水墨材料介入当下文化语境,无疑拓展了我们对于水墨图式革新的认识,也解构了历史的权威。
早在1980年代,张健君就开始用综合材料来创作。进入1990年代以后,张健君更多的转入了装置与影像作品。在2004年深圳水墨双年展的高名潞策划的“水墨空间”子项目中,张健君参展的作品是太湖石的行为和影像。张健君在墙上将一张宣纸覆盖在一张黑色的卡纸上,然后再用毛笔在白色的宣纸上画太湖石,于是人们马上会看到宣纸上太湖石的形象。但是等宣纸上的水痕干了,太湖石的轮廓线就渐渐消失,又还原为一张白色的宣纸。整个过程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了下来。高名潞评价张健君“画的过程,只是‘幻影’的出现与消失的过程。张健君把这个幻影过程用录像记录下来,但是,作为‘水墨画’的痕迹本身却永远消失了。”2高名潞认为张健君是在制造水墨幻觉,颠覆笔墨神话。 2011年9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举办了张健君的个展“水:张健君的行为、绘画与影像”,策展人是王南溟。这个展览虽然包括他的行为、影像、绘画及装置四个部分,但却属于同一个主题——时间与记忆、历史与人物。用策展人王南溟的话,就是这个展览“在互为阐释中生发出与‘水’有关但更与‘政治流水相’有关的想象空间。绘画中的水,影像中的水,及其一显即逝的人像,这些人当然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人物。但它与流水的绘画与影像拼贴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人和固定的历史事件,一切都在流水中被洗刷”。在本次展览中,张健君展出的也是以“水”为主题的作品,同时也会做关于“水”的行为和影像。张健君的作品,潜藏着一种伤感美学,一种诗意的残酷。当画中太湖石或是历史人物渐渐消失时,会让观者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或者说是对消失的焦虑。
王天德早期从事山水画研究,后来尝试将水墨的二维空间转到多维空间,开拓水墨的立体化空间表现,如创作于1996年的《水墨菜单》装置作品是王天德用着墨的宣纸将餐桌与餐具统统包裹起来,实现艺术家从“消费食物”到“消费文化”观念的转换。对于这件早期探索的作品,黄专这样评价:“这件作品进行了水墨艺术中由经典化文本(诗集)向世俗化文本(菜单)的转换;官方话语系统(御批)向民俗话语系统(菜谱)的转换,以及历史向度(水墨、书法)向当代问题的转换,它提示的问题是双向的:既批判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也提示了这种文本直接进入当代文化语境的可能性。”由此,黄专称王天德的水墨为“观念水墨”。2006年王天德创作了《孤山》,也是一件探索水墨空间的作品。王天德以西泠印社出版的一套书法碑帖为材料,他将碑帖焚烧成灰烬,堆积成一座座山的形状,然后用数码摄影拍摄下来,意喻传统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浴火重生。本次展出的作品《数码》系列,可以说是对水墨空间探索的延续,同时也是对高科技发展和数码时代的日常生活做出回应。他挪用山水和书法作为媒介,山水为底子,书法在上面,画面由两层叠加而产生新的水墨。但书法不再用传统毛笔或水墨而写成,而是用香烟烫成汉字的形状,从而形成一种“假”的书法。由于大多文字是不可读的,所以导致观众在观看时会产生新的信息,所以王天德称这类作品为Digital即数码。用焚烧作为创作的一种手法,可以说是王天德作品的一个符号。因为他认为焚烧有两个很重要的精神价值,一是中国传统水墨表现手法会承载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二是提出了水墨和书法艺术在当代数字媒体生存的方式。在王天德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考虑对水墨传统的关注或是水墨的观念性,而是通过摄影、装置等方式来重新诠释水墨在当代的可能性,着重于水墨痕迹与观念的表达。正如高名潞在《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一文评价王天德的作品“不论怎样观念化,王天德的水墨始终注重绘画性和美感,而且总能保持一种雅俗共赏的美感”。3
王南溟的作品更注重于问题情境中的思考。他早期作品从传统书法而来,《字球组合》是其1990年代早期的代表作。王南溟将写好的书法揉成球状,做成各种装置作品,使书法完全失去了可读性,而形成了另一种抽象形象。1992年,《倪卫华、王南溟作品展暨上海当下美术状态研讨会》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策展人是范迪安。范迪安在《反应与对应》一文中这样评论王南溟的作品,他认为:“王南溟以救赎式的虔诚触及书写行为,在连续书写与连续破坏书写结果的过程中,向传统文化的保守属性发出了深刻的诘难,并且剥离了书法的原有内涵,使书法媒介变为个人观念的载体。他的艺术既有观念上的冲击力,又有强烈的视觉特征。”42004年,王南溟、王天德与张健君都参加了2004年深圳水墨双年展的高名潞策划的“水墨空间”子项目。王南溟展出的同样是《字球组合》系列作品,不同于1992年的录像,这次展出的是字球装置作品。高名潞在《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一文中同样也评价了王南溟的作品,他认为:“王南溟所追求的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抽象画的物质性效果,而是如何将那种物质性转化到一种实际的‘生活化’的空间之中⋯⋯我们可以把王南溟的书法球装置看成批判的词语痕迹,同时也是建设批评法和艺术法的基础语词,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5本次展出的《字球组合》即是王南溟创作于1992年首展的录像作品,也可以作为一次对《字球组合》的回顾。王南溟通过对传统书法的解构表达了他的批评立场,这种批判立场后来发展成为他所说的“批评性艺术”。与《字球组合》同时展出的还有其1990年代创作的少字数书法,这些作品是将牵丝转化为线条,是对狂草书法的再发展。作品中书法的线被强烈地突出,而碑学的质感有线条的厚重,这两方面的结合创作的少字数书法,恰恰组成了以线为视觉的空间,运动过程中的飞白透出纸与墨的关系。在以线的运动为核心的艺术传统中,少字数的书法依然是个重要领域,尽管相比较《字球组合》,它还是平面作品。《孤云》与《鹤翔》等都是基于这样的方法而创作的作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也是王南溟创作《字球组合》的材料与媒介。
1990年代前后,陈光武开始了从传统书法向现代书法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他进行过各种尝试和练习,比如对汉字书写的错位、重复与叠加等。另外,陈光武特别擅长经营空间,他用涂鸦的方法让传统书法转换成现代抽象画,与那些只有笔墨游戏的现代书法迥然不同。2003年,陈光武参加了栗宪庭策划的“念珠与笔触”展,栗宪庭在策展手记中认为陈光武的作品“从童蒙习字——重复写一个字或一个笔划的方式中,发展出一种以重复写单字、偏旁、单一笔画、标点来结篇的书法模式。他的作品强调传统的一次性完成,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字或一个偏旁的一次性重复性写成。”6潘缨是从传统的工笔水墨画系统转向当代水墨。早在1980年代,除了少数民族题材,抽象水墨的风格在潘缨的作品中也同时存在。从1985年起,潘缨就开始了《虚构》系列作品的创作,这源于她对在平面上表达立体和空间结构的兴趣,同时早期工笔画的基础有效的体现在她的画面语言转换中。2010年,陈光武和潘缨都参加了由王南溟策划的“水墨的边缘”展,这是“上海新水墨大展”的子项目展。王南溟在《在“水墨的边缘”中的六个案例》一文中从材料的漂移性、语言的片断化和观念的针对性角度对陈光武和潘缨的作品作了评价:“陈光武的作品从反书法中来,将汉字作无法辨认的涂鸦,中间夹以逗号句号的标点符号。潘缨以丝带运动状态的各种结构为对象,用线条勾勒和墨色渲染出物质感。”7本次展览陈光武的作品《标点符号系列》与潘缨的作品《虚构系列》都是他们1990年代早中期的代表作。《标点符号系列》创作于1995年,整幅画面全用逗号和句号组成,这些标点符号既与书法有关,但又游离于书法从而自成一个系统。《虚构系列》创作于1997年,潘缨以“丝带”为表现元素,用勾勒的方法把丝带进行渲染,加以淡淡的墨色,把深藏于女性潜意识中的一面以纯粹的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丝带”或飞动,或打结,或自上而下,或从左到右,从而形成了属于潘缨的形式的、片段的、个人化的话语系统。
李周卫与刘永涛是本次展览中两位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当代水墨领域中的各种可能性。李周卫、刘永涛的作品都以都市水墨为主题,所不同的是李周卫着重描绘都市中的芸芸众生,突出对生命以及人生的思考。而刘永涛以表现都市空间为主,通过风景、建筑表达内心的精神诉求。2010年12月,我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策划了“透过风景+面对人群:刘永涛、李周卫双个展”,2012年9月,他们二人又参加了由王南溟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策划的“抽象之后的绘画:涂鸦、图像再造与多重主题”。在《透过风景+面对人群》一文中,王南溟认为“李周卫在中国画人物画的基础上作了一个大的突破,这种突破马上就让李周卫的绘画从人物写生式的单一画面,到与人物有关的形式创造。这里,人物不单独作为绘画主题,而且是作为观念的材料,李周卫是把那些活生生的人们组成不同的公众领地,让他们成为这些公众领地的道具。”8对于刘永涛的作品,王南溟认为“刘永涛把城市风景——建筑群纳入到画面中,建筑表面的完整性被揭掉,还原为裸露的框架,这就是刘永涛绘画中的城市风景。”9因此,刘永涛的绘画既不是泼墨的放大,也不是书法的放大,甚至于刘永涛的作品并不是非要用宣纸和毛笔才能创作。本次展出的李周卫《彼岸》、《现场》与刘永涛的《能够感觉到的风景系列》都是2011年创作的新作。李周卫用淡淡的、抽象的笔墨为我们呈现了长长的人群以及等候的茫然,而画面大幅的留白空间更是引起观者的无限遐想。刘永涛以浓缩凝练的线条,俯视的构图,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能够感觉到的风景系列。
本次展览主要讨论水墨画里面的核心价值:即水墨画如何在当代艺术中被提炼和更新。为配合“水+墨”展览,另设立主题为“艺术的东西方文化:解释与方法论讨论”的论坛,由王南溟主持,就这些话题再次进行深入的讨论,可次再次引发中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种种议题。虽然有关这些议题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但其中有些环节还有待于学理上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以便考察艺术中的东西方文化观的解释系统和它的理论背景,也有助于澄清这些问题在艺术讨论中的混乱。本次论坛设主题演讲与对话讨论,以期在学理上有新的成果。
注释
1巫鸿《作品与展场:论中国当代艺术》,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2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第三章《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P46,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3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第三章《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P45,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4 选自范迪安:《反应与对应》—倪卫华、王南溟作品展场刊,北京国际艺苑,1992年,同时见《江苏画刊》1993年第5期。
5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第三章《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P45,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6选自栗宪庭《念珠与笔触》策展手记。
7王南溟《水墨的边缘》,参见《水墨时代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8王南溟《透过风景+面对人群:刘永涛、李周卫的水墨画》,参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画册。
9王南溟《透过风景+面对人群:刘永涛、李周卫的水墨画》,参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画册。
【编辑:于睿婷】